散文精选 ▎母亲河上的箩脚子(文/孟宪佳)
母亲河上的箩脚子
文/ 孟宪佳
堤外北风头上的棚户区拆迁了,留下一片断壁残垣。
蔚蓝的天底下,高高河堤捧起的母亲河沱江闪着细碎的泪眼波光,静静地流向东方,默默汇入水天一色的洞庭湖。于是,水网密布的湘北平原上一条没有航标的河流,一脉客轮无踪的野水,从地图上无痕地消失了。四季分明阡陌纵横的平原沃野没有留住它,河岸上子女们深情的顾盼没有留住它。无语的送别中,只有伸到河滩的两座码头经年累月楞楞的不肯收回永恒的挽留。
这两座码头一座是粮食码头,直通堤内粮站的仓库。一座是煤炭码头,直达煤炭公司的煤坪。与今天钢筋水泥包裹的围城大堤相比,当年不分白昼,人头攒动的两座码头简直就是外河滩上隆起的两条土埂子。那年月,土埂子两边屋檐撞屋檐,甚至一墙隔两户的茅草屋就是箩脚子的家。箩脚子在山东泰山称为挑夫,在四川峨眉山、青城山叫棒棒。听先辈们讲,本地的箩脚子从前大都是“排牯佬”。民国早年,他们从上湘的山区伐木扎排,顺沱江的一条支流而下,成双成队地漂到我们这个洞庭湖畔的县城后,为了一年四季有白米饭吃就泊排上岸,在堤外河滩上立木为柱,结草为庐,向水而居。一根桑木扁担,一担篾箩,一间低矮的草屋,一个堂客(妻子)带三四个儿女就是他们的全部。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每年夏季沱江涨满水,运谷运煤的拖驳船靠岸,城内的人们纷纷扛起睡椅,提着竹凳到河边,看夕阳落水,摇动笆叶驱蚊纳凉。河面金波荡漾,河岸水风习习,乘凉的人扯着“程咬金三板斧”“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或“某某的满崽像叔叔”之类的闲话。尽管闲话的版本年年不同,但河边纳凉的风景年年依旧。
闲适的人自有怡人的风景,劳累的人却没有悠然的时光。与摇扇人相距不到200米的粮食码头和煤炭码头上,楠竹杆挑起的白炽灯下,身材矮小精瘦的箩脚子个个光着雨水不沾的膀子,脚蹬一双轮胎底麻草鞋,脖子上套一圈生牛皮垫肩,左手腕上缠一方粗白布,从驳船的跳板上结队鱼贯而下。码头上听不到人语,“嗨嗨”的喘息声,如抽动的风箱,弓样的扁担下堆得尖尖的篾皮谷箩和篾丝煤箩缓缓移动。扁担队伍实沉的脚步一步套一步,后者紧跟前者。走到大堤脚跟时,领头的箩脚子发出一声低沉的“调肩”号令,生牛皮垫肩上立马磨出吱吱的回响,身后队伍肩上的扁担齐刷刷地换肩。箩脚子们抬头看一眼比自己茅草屋高出许多的大堤,抬起手腕上的粗白布擦一把淋漓的汗。此时才看清他们黝黑脸盘上雪白的牙齿和突鼓的腮帮子。尤其煤炭码头的箩脚子早已被赤日和黑煤涂抹浸染得墨黑。他们肩上横着的桑木扁担透着深沉的乌黑,扁担下垂着的箩索也被黑汗渍渍的手摸得油光闪亮,装煤的箩筐更是黑得不见箩缝。长长乌黑的煤码头上如果不是煤筐在移动,很难见到还有能动的活物。一担煤足有一百七八十斤,箩脚子挑着比自己身体还重的煤勾着头上坡,喘息声越发急骤,后腿上古铜色的肌肉像鲇鱼肚子样地暴凸,牙根紧咬,汗珠子成串地滚落到厚厚的尘土上噗噗作响。远望去,黑色的码头上无声的箩脚子长队,就像煤矿里的皮带运输机,一头靠在煤船帮上,一头抵到煤坪里。满箩的一队从煤船上下来,空箩的一队走上煤船,无需机械能量周而复始地运转。
一担又一担,一船又一船。箩脚子不绝的脚力就是搬动谷山煤山的原动力。粮船和煤船渐渐上浮。粮站里成排的仓库被稻谷依次装满,煤坪里黑色的小山隆起一座又一座。半月当空时,河边摇扇纳凉谈今论古的人们还没有尽兴,码头上的灯悄然灭了。过不了一个时辰,箩脚子的茅屋里就传出了一片鼾声。箩脚子们摊开手脚沉沉地睡去,梦里还企盼半夜再来谷船或煤船,企盼明天不下雨。
摇扇纳凉的人大都不会顾忌明天的阴晴。在60年未溃过的县城所在地育乐大垸,他们以为只要家门口的沱江终年有水无患,从善如流,天上风调雨顺,幸福会从天而降。只有当他们每天揭开锅盖闻到诱人的饭香时,才意识到没有箩脚子箩筐中黄灿灿的谷,哪有碗里白花花的饭。只有当他们看见工厂的烟囱冒烟,厨房里煤火吐舌,冬日窗外飞雪时,才想起箩脚子箩筐里乌黑的煤,意识到黑色能源不仅淘汰了各家各户劈柴的刀,升起了小城的温暖,创造了小县城的“黑色文明”。
涨水横扁担,退水洗箩筐。挑箩为生,养儿育女。箩脚子自湘西老山里沿沱江漂落洞庭湖区平原,虽与城里人同饮沱江水,都是母亲河的子女,但由于他们文化程度不高,方言极不好懂,一种外来人的自卑浸入了骨髓,所以堤内堤外的人格格不入。既不隔山,又不隔水,围城大堤似乎成了棋盘上的楚河汉界,箩脚子与城里人无寸地之争,长期蜗居在城外堤下,守望着母亲河水的丰歉。在城里人畅饮自来水,甚至自来水管横过自家门的时日,箩脚子们也舍不得接一截水管,装一个水龙头到缸边,心甘情愿挑浑浊的河水用明矾净化后煮饭烧茶。如果将沱江水比作母亲的乳汁,城里人喝的是母亲的炼乳,而箩脚子吮吸的是母亲的初乳。在洞庭湖畔我们这个建县不足130年纯移民县中,第一个顶着呼啸南下的北风,第一个挡住浊浪排空的滔滔洪水,居住棚户区的箩脚子始终没能融入城内。他们深深地自悲,却没有破罐子破摔的自弃,更多的是自警自强。他们落地生根,勤劳节俭,吃得苦中苦,百事不求人,耐得住人间寂寞,向往辉煌的初心不仅代代传承,而且早已越过大堤,深深浸润到城内生活安逸的人群中,激励年青小县的后辈努力崛起。在本世纪涌现出的全国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飞机刹车片研制者,中国工程院黄伯云院士;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将军,就是箩脚子精神的光大者。
弹指间,年轮转过了七十多圈,江水永恒。近七十多个丰水的夏季,母亲河沱江年年忘不了给粮食码头和煤炭码头做一次洗礼,再温柔地离去。箩脚子分外地舍不得却又留不住东去的母亲河。沱江那无穷无尽的天上水是他们的生命之源,生存之本。老的箩脚子老在了沱江边,江水带走了一路走好的鞭炮声。新的箩脚子又生在沱江边,响亮的啼哭传出了茅屋,流淌的江水最早聆听了幼小生命诞生的宣言。
四季轮回,涛声依旧。家门口古老灵动的沱江或有夏季涌起的千堆雪,或有冬季凝成的三寸冰,浪奔浪涌之中荡涤出了箩脚子踏出的史辙。至今,到春天,粮食码头两侧仍有纤瘦的秧苗摇曳,那风中向往金秋的舞姿分明就是码头历史的象形文字。煤炭码头上,一层褐土一层煤,层层积淀,叠成了码头厚重的搬运史。在红黑斑驳的历史层面上,深嵌着草鞋脚踩出的两行乌黑的脚印就是码头历史清晰的脉络。
短暂的箩脚子断代史虽然没有留在庄重的线装书中,甚至没有只言片语的口传,但我相信今天挖下煤炭码头的一筐土,都能燃烧出光和热的火焰,并映照出当年母亲河上那群活脱脱的光膀铁肩历史人物影像——箩脚子。

作者简介
孟宪佳,湖南省南县人,当过知青,现为退休干部。爱好散文创作,作品散见《湖南日报》等报刊。2009年获得人民网“我与我的祖国”征文二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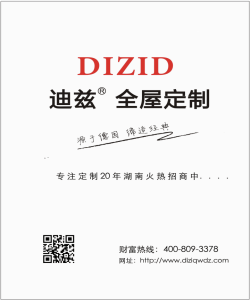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