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精选 ▎想起儿时望过年(文/高 尚 平)
想起儿时望过年
文/高 尚 平
先前,我们那里有句俗话,“大人望插田,小孩望过年”。我小时候真的特别望过年,不光是我,其他小伙伴也一样。
我地习俗,从腊月二十四小年那天起,就算开始过年啦!离年二十四还有好几天,小伙伴们便开始望过年了。只是都不记得日子,尤其是老历日子,脑子里完全没概念,要知道年二十四还有多少天,只能看日历。可那时日历也少,队上只有周会计家有每天扯一页的挂历。母亲说,周会计是个好人,我却怎么也看不出。周会计好像从不说话,也从来不笑,见了谁都脸一垮起,我们见了他就跑,就像见了队上的癫子“贱鸭”。到周会计家看挂历,一般是等周会计出工了,我们装着从这里路过,然后从他家堂屋穿过去。挂历钉在堂屋木壁上,瞟一眼就看到了。可惜有的小伙伴过两天又不记得了,有一年,我明明记得后天就是小年了,有的小伙伴却说是大后天,搞得我也糊涂了,只好又去周会计家看挂历。周会计是队上的会计又是大队会计,年终了要做账,有时出半天工有时半天工都不出,我们只好在禾场上远远地看着他,等他上厕所了再去看。好在每次都凑巧,一到禾场上,周会计就去上厕所,我们便迅速穿过他家堂屋。其实,我们那里家家户户腊月二十三都“打扬尘”。打扬尘就是将制蓑衣的棕和青竹桠绑在竹篙上,将屋檩屋梁上状若蛛丝的黑“扬尘”扫掉。如果今天家里大人打扬尘了,明天不就过小年了么!可每年的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周会计家看挂历,我们望过年啊!
说不清我为什么望过年。我望过年,或许是过年有吃的。
我们那里过年兴吃甜酒。无论家里条件多差,都要“拍”甜酒,队上除杨驼子家外,每家每户每年过年都“拍”甜酒。差不多过小年了,家庭主妇们见人就问糯米在哪里换,甜酒药子到哪里买。小年一过,小孩子们就开始串门。无论到了谁家,一进屋,主人就开始煮甜酒。当然,那时候的甜酒,一般都是半碗甜酒放半锅水,再放糖精,但我们就是觉得好吃,从年二十四到正月十五,几乎天天串门。一天去得几家人家的话,个个吃得肚子鼓鼓的,饭都不要吃。大人好像也爱吃甜酒,有年正月初八队上开工,第一组的人到边山嘴上挖桔树土,小憇时就近到五妹家吃甜酒,我一位堂兄就吃了十二碗,最少的也吃了八碗。
我最祈盼的,还是过年有肉吃。尤其是大年三十和初一初二,可以敞开肚子吃。尽管父亲对我们有严格规定——不能“打连拍锤”,就是夹菜不能连续夹两次,但只要桌上有肉,我每餐都会胀得“秧鸟几”一样。只是从初三开始,我家饭桌上便不见肉了。没出“上七”(初一至初七)的这几天,鱼还是有,可我那时只爱吃肉。凡有猪肉的菜,我都爱吃,比如肉骨头炖萝卜。我堂姐夫说,“萝卜煮肉好吃,肉煮萝卜也好吃,只有萝卜煮萝卜硬不好吃”,我觉得这话比语文书上说的更有水平。其实,父亲在世的那些年,我家灶上方每年都挂有一块腊肉,我估计至少有一斤,母亲却要留着待客。有一年,家里没来什么客,那块肉到插田了还剩一半,母亲就用坛子封起来。临近端午,那肉起滑了,母亲便叹声气,对父亲说,做给孩子吃算了吧。这时肉已变味了,吃起来像霉豆渣,可我还是觉得好吃。
过年这天,父亲还会做药豆子炖猪脚给我们吃,只是时间太难熬。每年过年清早,父亲就用铁炉罐将药豆子和猪脚炖熟了,放在灶屋的案板上,却一整天不给我们吃。离午夜只有个把钟头了,我和哥要睡得颈脖都直不起来了,父亲才慢慢把那炉罐提出来。看到炉罐挂到火塘梭筒铁钩上了,我和哥又振奋起来,只是要到凌晨,父亲才在阶基上点燃一小挂鞭炮,然后将梭筒铁钩上的药豆子炖猪脚取下来,一勺一勺舀给我们吃。所谓药豆子炖猪脚,其实里面只有一只猪手(就是猪前脚的膝下部分),如果吃时碰到一小坨猪脚或一个猪脚趾头,就会喜得不得了,觉得明年会走好运。
父亲是医生,除夕之夜让我们吃药豆子炖猪脚,可能有药理,可能是民俗,也可能是祈愿。只是不知为什么这时候才给我们吃,现在想来,或许有什么寓意,或许只是逼我们守岁。那时候,乡下人特注重除夕守岁。尤其是我父亲,他是通晚守岁的。我不愿意守岁,哥哥也不愿意守岁,吃完药豆子炖猪脚,我们嘴巴也不抹睡了。当父亲拿着一注香两支蜡烛三片钱纸和十八响鞭炮,打开大门“开财门”时,我们早已在床上舔着嘴巴做梦了。
过年还有茶食吃。茶食就是副食品,也是平常吃不到的。只是我家很穷,特别是父亲故去后,家里过年的茶食就只母亲自制的红薯片和弯豆麦豌了。不过,每年初一初二,母亲都要我和哥去给长辈拜年。我和哥见到伯伯叔叔姑妈,就按母亲的嘱咐,双膝跪下去。因家穷没礼送,伯伯叔叔姑妈不会留我们吃饭,更不会给压岁钱,但会打发一个茶食“封子”,或雪枣或南花根或寸金或焦切。那时尚有一伯两叔一姑妈,便能收获四个“封子”。茶食更要用于家里待客,但没出“上七”的这几天,母亲都会将待客剩下的茶食给我们吃,或一个雪枣或三个南花根,有时还加一片焦切或一根寸金。只是雪枣南花根因多次拿出来待客,早已拌得没“皮”了,焦切寸金也软了,巴手,粘牙,但甜味并没减少,还是好吃。
我望过年,或许是过年有看的。
那时候,有龙灯花鼓看。龙灯就是舞龙。龙是用红布制作的,两边用白布镶着鳞状的边。龙头和龙尾是用竹木做的,中间每约两米设一把,有九把的,有十一把的,还有十三把的。队上有两条龙,一条九把,一条十一把。每年正月十一一齐出灯,十五一齐收灯。我们队上舞龙全公社有名,不光每年在本队玩、到本大队其他队玩,有时还会被邻大队请去玩。我们队是个大生产队,有三百多户,每年舞龙都阵容庞大,气势磅礴。一支舞龙队伍,就有十多二十盏牌灯或鱼虾蟹灯开路,有四面龙鼓边打边行,持龙队伍有六丈多长,龙队后面还有响器唢呐助阵。
我爱看的是龙灯进入一家人家的场面。当龙即将进入某家,龙鼓便连槌连打,响器节奏加快,龙前耍珠叉的将珠叉一举,舞龙者便嗬哈喧天,箭步如飞,先从堂屋右边进去,从左边出来,然后穿过每一个房间、厨房,再到禾场上舞七八个“扭丝”,有时舞到十多个。这时候,主人家的鞭炮便煮粥一样放,看热闹的也尖起嗓子叫好。龙离开某家时,主人将早已备好的红纸“包封”向管物的“灯统”一塞,没准备“包封”的就给个茶食“封子”。若是住户紧密相连,耍珠叉的又将珠叉一举,舞龙者便又嗬哈喧天进入另一家,我和小伙伴们便跟着赶到另一家。
花鼓是地花鼓,俗称“花鼓子”。地花鼓如戏如舞,如东北的二人转,由一旦一丑组成,只是旦角我们那里叫“妹子”。“妹子”的装扮很讲究,头上戴着凤冠,多是银制的,衣服是特制的古典服装,肩上还披有闪闪发光的饰物。道具却很简单,就是丑角持一扇,“妹子”拿一帕。表演也不复杂,无非一男一女扭来扭去转来转去,俗称打“窝子”。但那时都喜欢看,比如我母亲,队上的地花鼓耍到哪里她赶到哪里,外地的地花鼓来了,也每场必看。不过她看地花鼓不是看表演,也不是听唱腔,而是看扮相。如果这年的“妹子”扮相好,她就说今年的花鼓子好看。我也喜欢看花鼓子,但我喜欢看的是丑角,搞笑。丑角的脸上,都用白颜料涂三下,一般是鼻子上涂一线,脸上一边刷一块,就像刚学写字的孩子写的“小”字,一看就忍笑不住。
我们那里的地花鼓有许多固定曲牌,大都很好听。如采茶调、望郎调、卖杂货,加上胡琴、笛子、唢呐、响器配合,更是动听。唱词也多恭贺、祝福之语,如“送财”“送子”“辞东”,都吉祥喜庆。即便是一些男女情爱节目,也乐而不淫,很有生活韵味,极受民间欢迎。有的人家,外地来了地花鼓,也拦在路上去请。
龙灯和花鼓,有单演的,也有合演的。合演一般是应主人特邀而为,比如某家这年正月收了新媳妇,主人便会邀请队上的龙灯和花鼓一齐到他家演出。龙灯和花鼓进入这家,耍花鼓的就专演“送子”类节目,在禾场上演,在堂屋里演,还特别在新房里演。耍龙的送子节目更有套路,我印象最深的,是将龙绾成莲花模样,托着一个小男孩到新房里舞来舞去,再到新娘床上怎么怎么,叫做“麒麟送子”。龙灯花鼓合演,场面煞是壮观,大人小孩蜂拥而观,禾场上围得水泄不通。
只是,龙灯花鼓都是闹元宵的项目,至少要到正月初十以后才有看,过完元宵节就没有了。能看龙灯花鼓的日子,一年总共就只五天。
当然,正月十一以前也有很多看的。舞狮子啦,赞土地啦,三棒鼓啦,都是初一就有了。我们队上年年有舞狮子的。队上有个五机匠,老婆年近五十怀了孩子,难产,本是大人孩子都保不住的,两个赤脚医生和几个接生婆拼命抢救,将大人保住了。这事发生后,五机匠便邀他外甥年年正月间到各家各户舞狮子。狮子舞得活灵活现,花样百出,可他一不收“包封”,二不收“封子”,就连抓把瓜子花生也不受。“赞土地”也是正月间常见的民间节目,由一男子提一小锣,到一家人家就边敲边“赞”好话。一般只按套路“赞”,主人给他五角钱,就走了。有的则将主人家的特点即兴编出“赞”词,给他五角钱不走,再给他五角钱还不走。三棒鼓类似赞土地,却很有功夫,玩者到了某家人家,先张开鼓架把小鼓架好,然后手持三根七八寸长串有许多铜钱的小棒边敲边唱边向空中抛舞,舞到最后,还将小棒换成三把锋利的尖刀,抛舞节奏逐渐加快,看的人便不停地喝彩。不过,这种节目我地只有赤山人才会玩,其他地方的人是玩不了的。
也有我不喜欢看的,比如划“家龙船”,我就觉得没什么看头。划家龙船,就是一人腰上挎着一个米把长的彩色“龙船”,穿得五颜六色,脸上画着花,像端午龙船上的“辣蓼婆”。手持一小桨,到人家堂屋里划来划去,口里一边叨念,像念像唱,不知说些什么。每当家里来了划家龙船的,我就对母亲说,快给两角钱让他走吧!我不喜欢的,还有送“正当行时”。送“正当行时”是将红纸裁成不足一寸宽约三寸长的条条,上面用毛笔写上“正当行时”四字,家家户户去送。主人收了条条,就给五分或一角钱,然后贴在门上。那时过年,送“正当行时”的很多,不过我们队上没有,全大队好像也只几个人送。常来我们队上送“正当行时”的,是湖区那边的,再就是邻队的福跛子。
我望过年,或许是过年有玩的。
我最喜欢玩的是耍清洁龙。清洁龙是小孩子玩的,当然,太小的孩子还是玩不了,一般是七八岁到十五六岁的孩子玩。清洁龙又叫草把子龙,龙头、龙身和龙尾都是用稻草编制的,“把”也不是木的,而是青竹棍。一般是七把,也有五把和九把的。年纪小的玩五把的,年纪大些的就玩九把的。也是正月十一出灯正月十五收灯,但不固定的,多是几个小孩子凑到一起,正月十四或十五临时起心,就制一条草把子龙到各家各户去耍,只是无论哪天制草把子龙,元宵节收灯后都要烧掉。我小时候,几乎年年要耍清洁龙,从七八岁耍到十五六岁。耍清洁龙一不要龙鼓,二不要响器,因是白天玩,也不需灯,整个队伍就只舞龙的几个孩子。如果是耍七把的清洁龙,加上耍珠叉的和“灯统”,总共就只九个人,有的就连“灯统”也是由耍珠叉的兼的。耍清洁龙虽然简单,乡下人却很看重,认为清洁龙喜庆、吉祥、祛邪。尽管只是几个孩子,清洁龙到了某家,主人都像接待布龙一样放鞭炮,给“包封”。“包封”当然不大,一般是五角,也有八角或一块或给个茶食“封子”的。有年第一次出灯,恰逢一家人家收媳妇,便封了一个两块的“包封”,喜得我们总是要“灯统”拿出来看。当然,也有一角两角的,还有一分钱也拿不出,只能抓一把红薯片或弯豆子的。
不管有无“包封”,无论“包封”大小,我们耍龙一样卖力。杨驼子家几乎每年都靠到队上支米过年,又住偏远的郭家嘴上那破茅屋里,我们每年照样将清洁龙耍到他家,从不收他什么。不料有一年耍到他家,他母亲却给了个“包封”。我们哪能要他家的“包封”呢,他母亲打架一样要我们收下。当然,他家的“包封”不可能很大,“灯统”搣开红纸一看,里面是五分钱。但我们接到这“包封”,感觉如两块的“包封”一样客气,甚至比两块的“包封”更沉甸。
到队屋里玩响器,也是我过年的重要玩项。响器就是打击乐,队上有两套响器,平素锁在队屋的保管室里,正月初四五里就拿出来供排练龙灯花鼓用。排练龙灯花鼓并不需时刻用响器,有时甚至一整天也用不上,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趁机去玩。爱打鼓的打鼓,爱拍镲的拍镲,爱敲锣的敲锣。保管员叫双喜子,平素很凶,见了我们便当贼防,我们从队屋地坪走过他也朝我们吼:又来搞么子!而过年这段时间去玩响器,他却满脸堆笑,还耐心地教我们玩。每次我们才到地坪,他便将鼓往屋中一架,开始给我们示范。只是他玩响器的水平比我还差。一套响器有五件,一鼓两镲一小锣一大锣,镲又分前镲和后镲,双喜子一件都玩不好。我们也不说破,得空就去队屋里玩,有时玩得饭都不想回去吃,后来,有几个伙伴还成了打击乐高手。那年学小靳庄,双喜子见公社文艺宣传队搞打击乐的几乎都是我们队上的,就很得意,有回还对大队支书说,那都是我的徒弟哩!
过年下雪的话,还可以踩高脚,扮雪菩萨,用鸡罩子罩鸟。高脚就是高跷,我们自己做的。每当下雪,我和小伙伴们就集体出动,踩着高脚到处玩。扮雪菩萨有两种玩法,一种是将雪堆起来,塑成人像或动物,一种是将人身摆成不同姿势向雪上猛摔下去,在厚厚的雪地上印出不同样子的“菩萨”。只是这两个项目我都玩不好,我玩得好的是用鸡罩子罩鸟。
用鸡罩子罩鸟,就是将家里关鸡的篾制鸡罩放在禾场上,下面放些谷物,用绳子拉得张开一边,等到鸟到了鸡罩下面,将绳子一松,鸟就被罩住了。玩法和鲁迅《故乡》里写的相仿,只是工具不同。有时一天罩得好几只,有斑鸠,有麻雀,还有一种比麻雀小的鸟,运气好的话还会罩到粪屎八哥和山鸦鹊(就是那种红嘴巴喜鹊),不过粪屎八哥和山鸦鹊都是很难罩到的。
我们罩了鸟并不吃它,只是玩它几天,喂它几天,天气一晴,就把它放了。有的鸟,放了还会回来。有一回,我罩到四只斑鸠,喂几天后,就在它们身上涂些红墨水放了。过了几天又下雪,其中两只又回来了。这天家里恰好来了一个亲戚,见我在喂斑鸠,就对我母亲说,你们家养了鸽子啊!
我过年所望的,或许就是这些,或许不止这些。当然,现在看来,这些都不值一提,但那时候却是我一年一度的盼头。有盼头就有喜悦,有盼头就有快乐,人生或许也是这样吧!

作者简介
高尚平(笔名“崔信”),湖南省沅江市人,现居广州增城。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广州市职工艺术家。1981年至今,在《湖南文学》《星星诗刊》《微型小说选刊》《广州文艺》《散文选刊》《当代人》《西部散文选刊》《湖南散文》等报刊发表文稿数百篇,约100万字,出版作品集《高尚平近作选》(上下册)。曾获湖南省第二次青年文学竞赛一等奖、沅江文学创作一等奖、湖南省报纸副刊作品一等奖、第十七届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三等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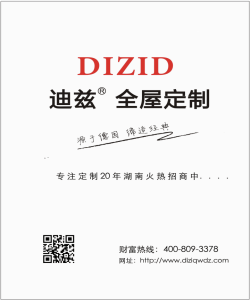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