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精选 ▎人 生 草 木 间 (文/王祯辅)
人 生 草 木 间
文/王祯辅
茶,素常之物,开门七件事之一。可到了文人雅士口中便谓之“品茗”。家乡管喝茶叫“呷茶”,呷,小口小口地喝,多到位多传神。要说传神,我不得不敬佩我们的老祖宗,造个“茶”字,从草,从人,从木,人生草木之间,陡然几分烟火之气萦绕开来。《茶经》云:“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家乡地处湘西南雪峰山区,有关茶事也就稀松平常了。 家乡地貌多样,山地、丘陵、平原兼有。气候温润、雨水充沛,土壤肥沃,很适宜茶树生长,历为名茶产区。清光绪三十四年《武冈州乡土志》载:“茶常产本境西北(今洞口县境内),山土最宜,岁可产数万担。”《武冈州志·贡赋志》记载:“茶铁竹木之饶,最于黔粤。”“货之属则有棉花、木炭、石炭、蜜、茶、楂油……”注:“(茶)峒产甚佳”。峒即峒蛮,旧时称南方少数民族。《武冈州志》里所说的峒蛮全部在今洞口县境内。据我所知,洞口产茶以古楼、茶铺为盛。古楼地处雪峰山腹地,山高林密,溪流潺湲,常年云雾缭绕,山岚润泽。这样的环境为云雾茶提供了上好的生态条件,明洪武十八年(1385)古楼盐井茶被朝廷列为贡茶,从此古楼茶声名远播。茶铺属古镇高沙,地处古驿路要道,自古产茶地,建有店铺茶亭,行人憩息饮茶于此,故名茶铺子。依托交通的便利,湘黔古道穿境而过,唐宋时期在洞口、高沙就设有驿站,元以后,以洞口为起点的商旅常行古道有五条,以高沙为起点的商旅常行古道有四条,当地的茶叶等物产得以远销武汉、上海诸地。此地产的青茶,泡出来汤色碧绿,栗香馥郁。万物复苏,春暖花开时节,借一涧清澈春水,冲泡一杯明前茶或雨前茶,顷刻间,杯盏之中云雾蒸腾,汤色如同绿烟,嫩芽复苏舒展,上上下下,沉沉浮浮,暗香浮动,人便思绪飘于云外,仿若置身山野之间。那时节,杯中之物已不再是茶,简直就是一杯春色!
我本不太会喝茶,对茶道鲜有研究,但对茶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道的态度颇为认同。茶可变形,能屈能伸。在山野,茶叶吸日月精华天地灵气,满目青绿,一派蓬勃葱茏,经揉炒杀青后,蜷缩成团,如隐者一般皈依寂静。当一股沸水迎头一浇,雀舌也好,龙团也罢,随着热汤翻滚,一片一片都会舒筋活络,凤凰涅槃般华丽变身,有如从幽暗处款款走出的佳人,再现姣好容颜,重新绽放自己的美。尘俗无由牵,该隐则隐,该显则显,须经得起磨砺,耐得住寂寞,于水深火热之中不易其志不改本色,一切如云卷云舒,收放自如。
“寒夜客来茶当酒”。茶是否能当酒,应另当别论。酒有水的形态,却暗藏火的性情,水火不容。因此酒须武斗,吆三喝五,赤膊上阵,面红耳赤,放浪形骸之外;茶亦有水的形态,却是草木青葱之貌,温婉如少女,水木清华,仪态万方。因此茶须静品,可邀三两韵友浅斟,又可一人独啜,雅意入怀,茶禅一味,如坐春风。酒宜歌,击节划拳,慨当以慷,呕哑嘈杂,纵情豪放。茶宜乐,七弦横陈,余音绕梁,缱绻低回,意味深长。酒有一种江湖气,讲情讲义,有胆有识,一股侠气贯穿席间;茶有儒雅之气,关公巡城,韩信点兵,看似关乎武事,实则文雅之极,讲究一套一套的礼数。由此可见,酒以义取,茶以礼胜。我特别想往那么一种喝茶的状态,就是“找个老茶壶,约个老时间,几个老朋友,磨个老半天,胜过活神仙。”这样喝出来的茶还是茶的味道吗?那是本我的味道,是乡土的味道,是人生的味道,是天地的味道。个中滋味远离当下,思接千载,可以接近苏轼,可以接近卢仝,可以接近陆羽。
茶有雅致的一面,也有民俗的一面,家乡产的银针、毛尖、春芽之类青茶,近些年来经过包装后价格也就不菲了,但普通百姓居家过日子还是粗茶淡饭,仍然保留着朴素的民风。雪峰山深处的挪溪瑶乡的“熬茶”别具民族风情。上网查阅了一下,关于“熬茶”的词条不多,以青海熬茶最为有名。青海熬茶是一种煮开的红茶,是用川湘茶区出产的砖茶加水煮开,再加上青盐、花椒,讲究点的还要加上姜皮、金芥。挪溪“熬茶”截然不同,挪溪有句俗话:“上五里喝熬茶,下五里讲瑶话。”说的是上五里宝瑶、宗溪、白焦一带瑶家独有的喝茶习俗,起于何时已无据可考。熬茶的茶叶是采摘山中谷雨前茶树的嫩叶,揉三遍,微火炒三遍,再搓成蚕豆大的茶团,放入篾筛里挂在火塘顶上炕熏。熬茶时用的是几代人留传下的茶锅,大部分人家是用烂生铁鼎罐底部敲制而成,看似粗俗得很。平素来客,主人将茶团放进锅里,加水反复煎熬出黑褐色很浓很香的茶汁,再斟入茶盏招待客人,这是瑶民待客的最高礼遇了。这种茶入口苦涩,入喉回甘,能消渴解乏,喝后成瘾。如待新客就会往茶里撒些冰糖或红糖,这与青海熬茶加盐和花椒不同。
以茶的熬制过程命为茶名者,实不多见。说到“熬”,足见瑶民的率直豁达,表述也是如此的浅白有真意:长长短短深深浅浅的日子得慢慢熬,把时光分割成段落,熬过初一,又熬过十五,将一切苦厄熬淡,熬到苦尽甘来;融洽的人事也得文火细熬,熬到烂熟于胸,水到渠成,熬到明心见性,修成正果;美好的情感也从熬中得来,年轻的媳妇熬成婆,少年到白头,把原汁原味的生活熬得水乳交融,如胶似漆。不管五黄六月,地涝天旱,得熬。熬是乡民的坚忍,他们如草木一样,烈日炙烤,霜冻雨打,野火焚烧,熬住了,挺住了,来年开春,还不是一茬一茬萌发出新绿来。
熬茶的茶叶常年挂在火炕上,像挪溪腊肉,烟雾熏烤,经年不坏,较之现今将茶叶贮藏冰箱之法大相径庭。依此法炮制的熬茶质地丰厚,滋味浓烈而近乎粗野,有劲道,如陈年佳酿,如边塞诗词大气磅礴,亦如当地民风,慷慨质朴。宝瑶原是湘黔古道上的驿站,西接黔阳,明清时期热闹繁华,过往商旅络绎不绝。瑶民们敞开襟怀,迎来送往,大方地唱着敬茶歌,递上一杯杯热气腾腾的熬茶,艰涩的茶味如同旅味的苍凉,苦涩过后的醇厚绵长又如瑶家的款款深情。打此西去,便到洪江,当年边塞诗人王昌龄左迁龙标(今洪江黔城),并在这一带山水之间写过一首送别诗:“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因此,每每喝到熬茶,便会隐隐感到熬茶蘸有唐诗的味道,再细细一品,又能品出瑶民的一片冰心。如今湘黔古道已经废弛,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一切复归平静。在瑶民赋闲休憩或劳作之余,也许在充满草木清香的正午,也许在炊烟袅袅的傍晚,熬上一锅茶,消闲解乏,喝着喝着就会有一缕山野的风习习而来,又仿佛听得一曲野腔野调的瑶歌回响在大山深处,因此树木更绿了,大山更深沉了,这方水土这方人也跟着静谧和安逸了,一时间风轻云淡,大地静好。
家乡有些地方管操持家务为“舞茶饭”,说到舞,既状其形,又状其态。煮茶做饭需要打脚舞手的繁复工序到堂,舞出来的结果是家常的,也是艺术的。奶奶舞茶饭很里手,能把紧紧巴巴的日子舞弄得有滋有味。奶奶常说:“乖态莫过素打扮,好呷莫过茶淘饭。”茶淘饭不见得好吃,在锅里碗里难得见到油星子的年月,能将干冷的米饭送下肚去也只能是寡淡的茶汤了。这种淘饭的茶是家乡一种叫“棉花茶”的叶子煮出来的,这种茶只需两三片茶叶放入沸水里煮,煮出来色泽泛红,口味略显粗粝,却也有点回甘,入夏随时煮一鼎罐棉花茶,盛入瓦罐里搁置阴凉处,就算存放三四天茶也不会变味,口渴了拿长柄竹勺往瓦罐里舀来喝。
棉花茶应归于凉茶一类,棉花茶不含任何添加剂,数日而不变质。也不像其他瓶装茶饮,其色艳俗,其味暧昧,棉花茶只有草木的本色本香,只有寻常人家的寒素之风。盛夏时节,天气酷热,引车卖浆、肩挑背驮者打家门口过路,上门讨口茶喝的经常有,奶奶就用棉花茶相待,他们不讲斯文,毫不客气的引颈牛饮,来一碗,又来一碗,茶水顺着嘴角往下流,打湿了衣襟。一旁奶奶笑吟吟的看着,忙说慢点,慢点呷。人人都说烟酒不分家,其实在家乡茶水也是不分家的,讨茶者不管上哪家歇脚,都会有好茶好水招待,没有繁文缛节。歇一肩,喝完茶再走,脚步也轻了,行囊也轻了。人走在路上谁没有过难处,全凭茶水长精神。遇到久旱或苦夏,奶奶索性把茶罐搬到屋外,任过路客随便喝,以解劳顿口渴之忧。施茶在小镇高沙随处可见,有古风,见佛性。
奶奶很惜顾,常说惜顾饭有饭呷,惜顾衣有衣穿。就连泡过后的茶叶,她也不舍得丢弃,收集拢来,晾干,灌到枕芯里,做成茶叶枕头。夜晚,睡在茶枕上,茶香就会徐徐散发出来,连梦也清新起来了……把中药汤子叫做茶的,也是从奶奶那里听来的,要是有个头痛脑热的便说去拣副“茶”来呷,拣回来的却是一副“中药”。后来我想,也许是奶奶忌讳,希望日子过得顺顺遂遂、平平安安、健健旺旺,不愿提及“药”字吧。
最初,茶是作为药用而进入人类生活的,《本草》中写到:“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忽然想起以前读过的一篇文章,说是周作人的作品是茶,鲁迅的是药,回味一下,觉得还有点意思。这样说来,到底药是茶,还是茶是药呢?人生草木间,有些事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作者简介
王祯辅,现供职于国家税务局总局洞口县税务局,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散见《湖南文学》《中国税务》《邵阳日报》等报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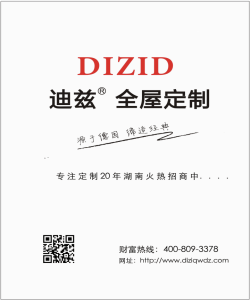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