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精选 ▎他 们,或 薄 凉 的 尘 埃 (文/周伟)
他 们,或 薄 凉 的 尘 埃
——驻村扶贫手记
文/周伟
在那片生生不息正在行进着的土地上,他们和他们的故事,经月流年,亘古恒新,庄稼轮茬,苍翠更迭。
我在下派赖梅驻村扶贫的近一年时间里,常常感到手足无措、乏力,心有戚焉,爱忧悲愁俱来。
是的,面对如亲人的乡民,我多想拥抱你的贫寒,握住你的薄凉,安抚你的沧桑,燃烧你的梦想。
每个夜晚,在路上走着,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在竞相盛开,光芒蔓延。
每天清晨,走在路上,望春风,尘埃与太阳一同冉冉升起,看田野的画廊,看生活的春光,看生命的盛宴,为幸福而歌。
1
大伙都说,唐云花是个心气高的人。
她很少与大伙来往,也不屑与大伙打成一片。刚嫁过来,她和丈夫两个人同出同进,田里地里,山上山下,屋前屋后,忙得尽兴、温馨。那时,家里也搞得小红火,还起了红砖房子,屋的正面还贴了白瓷砖。
村子里的人大多是起的木架子屋,就有很多人妒羡她,说这小两口是在摆脸子,做给大伙看。大伙又说唐云花,一个农村女人,把自己打扮得花一样,她屋里的那位把她当宝一般。她自己呢,还真以为自个儿浮在云端上,还不是和我们一样,田里土里,山前山后,和着泥巴过日子。
于是,唐云花这户搞来搞去,终是没能评上贫困户,最终只定了个边缘户。
慢慢地,生了孩子,一儿一女,家里就稍稍有些紧巴了。特别是女儿,竟有些精神恍惚,不正常。唐云花急在心里,就带了女儿去了深圳。她一心想着把女儿的病治好,住了一个多月,实在没有钱再住下去了。唐云花说她心痛的也不是钱,心痛的是女儿的病不见好,吃了药,一下子胖到了二百多斤。她搂着浮肿发胖的女儿,眼泪止不住地牵线线流。深夜里,她一个人跑到空旷的广场上大哭了一场,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她的哭,是哭自己的钱不够,哭女儿的病没有起色,哭自己的命苦……
哭完,她擦干眼泪,又去厂里出工,把女儿锁在厂部的宿舍里。下了班,她风急火燎,急匆匆地往宿舍里赶,怕女儿饿了,怕女儿尿了,怕女儿摔了,怕女儿哭了,也怕女儿闯祸了。女儿的病愈来愈重,常常就在厂部的宿舍里哭着笑着闹着,唱着跳着叫着,有时见东西就摔,见衣服就撕,见人就骂,还常常把人家女工花花绿绿的裤衩套在自己的头上……没有办法,唐云花只得带着女儿回家。
女儿的病时好时坏,唐云花在田里干着农活,就要时不时牵挂到家里。她仿佛练就了一身本事,眼睛能看到几里外的女儿,耳朵能听到几里外女儿的声音……常常在田里地里忙得正起劲的时候,她忽然发疯似地往家里跑,一边跑一边说:不好,女儿有事了!好在,她总能够及时赶到。也怪,女儿见到了娘,常常就不哭不闹,不跳不叫了。
她也真是命苦,去年她的儿子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在高速路上私拆测速仪,被公安拘留了。后来,村委会出面讲情做保,她的儿子才被放了回来。
她是个好强的人,也是个肯下力的女汉子。她说她和老公就是拼出老命来,也要撑起这个家!她和老公起早摸黑,种了四十亩水田。女儿的病不能不管,一年要到县里的精神病医院住三四次,花的钱不是一个小数目。不料,不久丈夫突患食道癌去世了。丈夫死了不久,有好心人看她这个家里确实难撑,就介绍一个离了婚的男人,尽管没有扯证,却也里里外外多了一个帮衬,唐云花的心里也平静了些。
可好景不长,偏偏今年前两个月她家里又横生出了一场车祸。她的男人骑着一辆摩托,和一辆私人的小车撞上了。尽管大部分责任是那辆小车司机的,但她男人却因没有办理摩托车驾驶证,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唐云花跑上跑下,顾前顾后,忙里忙外。她说,再难再苦,也是我的命,男人就是瘫了,断不能甩手不管,也要养起来!
那天我看见她左手上有一个好大的疮疤,肿得透亮,还流出了脓。她有些艰难地拖着右腿,说前两天在田埂上摔伤了。我问她男人和女儿的事,她却跟我说,田里要收谷子了,何得了?这个节骨眼上,何得了?!我说,赶紧请人吧,可不能把谷子烂在田里。她说,嗯啊,要不然,一年的心血和收成就打了水漂了。她看起来很心痛,脸上瞬间难成了一块焦躁的土地。
她说,请人得付工资呀,这四十亩水稻收割下来,没有八千元是万万不行的!又说,真是毫无办法,你们工作队能不能帮帮忙?我说,你马上打一个报告,村委会签字盖章后送到镇政府民政办去,多少能批一点,你这边该请的人马上请,一点儿不能耽搁,一点儿不能含糊。
第二天,唐云花又来到我们工作队的驻地,说昨天去了镇政府,没有找到书记和镇长,民政办主任也休了假,交给了一位工作人员。她担心地说,怕是也没有多少用处呢。我们宽了宽她的心,说,我们也去说说,等一等,多少是有点用处的。现在,最紧要的是赶快把谷子收回来!
她点点头,不时地说:唉,我这个命,真是气死人!看得出,她是个好强的人,心有不甘。我再扫了她身上一眼,发现她尽管这么艰难,一身的打扮还是不邋遢,衣着穿戴,整洁好看。
我说,你这个情况,手上、腿上都有伤,也下不了大力,还是要靠儿子多出点力……没等我说完,她又说起儿子,说儿子也不容易,晚上要去县城里上夜班,白天还要赶回田里地里帮忙。又说儿子的心情也低落得很,在浙江打工的儿媳和他刚刚办了离婚。
过了一阵,唐云花看着窗外,说了一句没由头的话:明年,真的不想种田了!瞬间,又把抛出的话生生地扯了回来:唉,不种田,又能做什么?我不知道,她是在问我,还是在问她自己。我实在没有想到什么好法子,能立马打消她的悲叹和痛苦。我赶紧避开了她的目光,去看屋前大片黄熟的稻田,心里甚觉过意不去。过了一阵,她又喁喁地说:实实在在的,也只有田了——田,是四口人,是我们四口人的命根子呀……
我看着她,想起她犯浑的儿子、疯疯颠颠的女儿和瘫在医院的男人,特别艰难的一家四口,不由得心里深深地刺痛了一下。我再次避开她的目光,放眼望去,屋前大片肥沃的田地,遍地黄熟,热浪翻滚,风过处,五谷飘香,稻谷笑弯了腰,甚是喜人。远处,旷野大地上有几个小得像蚂蚁的人影在忙碌着,生动着……在眩目的阳光映照下,一个个挥汗如雨,汗水晶亮,风一吹,立马风干成生命的盐和不涸的希望。
唐云花下楼去了,一步一瘸,走进黄灿灿的生命图腾里。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的心里很不是个滋味。此时,有一线阳光直直地射向我,灼痛了我的眼。
有好长一阵,没见到唐云花,每回经过她家,只见大门紧闭,我的心里好像丢了什么似的。我总忘不了这个叫唐云花的女人,忘不了她的眼神。
有几次在村部向村干部问起她,村主任说在县城里碰到过她。村主任说她向他羞涩地借过两回钱,说自己的男人还在医院躺着,说自己的女儿也在医院躺着,花钱流水一般,手心里实在生不出钱来。
我更关心的,是她种的四十亩水稻制种。听村主任说,好在镇政府解决了一些工钱,请人终于收了回来,没有烂在田里。村主任还说,她家今年也获得了不少的种田补助和奖励,还享受了大病补贴,情况会慢慢地好起来。
更有好消息传来,说她家的情况不用评,有可能直接由边缘户转为贫困户,将会得到政府更多的帮扶和补贴。我替她高兴,告诉她。她却不喜不惊,不愠不火地说:我就不相信,自己一辈子就是个苦菜花的命?!
我看着她,看着她脚下肥沃的土地和生生不息的庄稼,看着她风风火火不服输不信命的样子。我想,再薄的命,毕竟在乡村还有肥沃深厚的土地,平凡却深埋力量。有土,终会有希望;不信命,就会在土地里开出花。有道是,天地氤氲,万物化醇,万物化生。
我离开驻村已有半年有余,却不时想起村子的人和物事,是那样的清晰、真切和生动。他们的故事,令人心痛却不悲观,坚韧地默默地活着是他们的本色。就是泪流干了,头也不回,心也不死。他们总是认定:生活的希望,生活的美好,总在前方;路还长,天总会亮的。
在我眼里,总出现那么一幕:太阳仍是每日早早地升起,那个叫唐云花的女人衣着穿戴整洁得体,红红绿绿,云花开放。她的头上,还自然地夹了一个向日葵的花夹,迎着阳光,甚是亮眼。
她依旧日日迎着太阳出工,缓缓地,一步一步,往山腰上的水田里走去。定睛一看,太阳下的生命,草疯长,云花开,路伸展……
2
那天,我和村支书等人上门,见大门紧闭,喊了几声没人应声。有人说,老人在对面的石桥上歇凉。我们走过去,还没开口,就受了这个老人一顿怒火。村支书却不恼,随他发泄完,然后跟在他的身后从石桥上走过。老人一身黑衣打扮,干瘦如柴,眼睛深陷了下去,看样子视力很受影响,拄着一根拐杖,滴滴啵啵、滴滴啵啵地一路响个不停。
村支书说,老人发这么大的怒火,其实是有原由的。他其实是个硬气的人,从不向镇里、村里“伸手”,再苦再难,也不叫苦,也不喊难,就是不给他评贫困户,他也不会提意见,更不会去镇里县里上访。但是有一个事,他却发了很大的火,当年纳入贫困户,也可以不是整户登记贫困户。原来的村主任考虑到他的儿子还能出外打一点工,就给他家登记时,只登记了两人。这一来,曾令友就认为大不吉利,把他家人口减少到两人,会出大问题的。没想到,一年后他的老婆去世了。
许多年后,曾令友一直固执地认为,是因为村里登记时少登记了一口人,才导致他老婆不幸去世。所以,自此以后,他一直对镇、村干部和工作队意见很大,经常不配合,一说起人口就大动肝火,满腔仇恨。
他家的老木屋,现在歪歪斜斜的,破旧不堪,符合危房改造,但他仍然坚决不同意,说,我家的老屋是祖上留下来的,而且是村里有名望的老木匠精心打造的。老屋修好后,老木匠私下里一本正经地跟他说,这老木房是断断动不得的!他相信老木匠的话:老屋的风水不能动,一动就会不吉利,会出事。
但是,村里这一处危房不改造,将会影响到贫困村的退出,也会影响到全镇的脱贫检查,当然更会影响到贫困县的退出。这样,就显得特别恼火。镇危改办主任、扶贫办主任、副镇长、副书记、镇长、书记,都几次三番登门,都做不动工作,收效甚微。曾令友双眼半睁半闭,一根拐杖横在门槛上,谁也不敢跨过半步。
后来,还是村支书拍了胸脯,想出了办法。他做动了曾令友儿子的工作,并且拍胸脯说危房改造不要他儿子补一分钱,政策解决后的不足部分概由县里、镇里、村里承担。然后,就不动声色地要他儿子接了他父亲去了县城医院好好地检查检查,多住几天院。这边,就在老屋旁边下基脚起屋,加班加点。待曾令友回来时,老屋没拆,新屋也起得差不多了,粉墙盖瓦刷地安装好门窗,大功告成。
赶在检查前,县里镇里要求贫困户个个必须要搬进新居拆掉老屋。曾令友起先是坚决不肯把床搬进去,要搬只把锅碗瓢盆搬进去,他说自己的正屋还是老屋,这新起的屋最多算个拖屋、厨房和厕所。于是,镇里领导下了死命令,不管好说歹说,无论是来软的还是来硬的,反正一句话:抬也要抬进去!新屋里必须要有床,要见人,要有烟火味和幸福喜庆的模样。
光是幸福喜庆的样子还好办,买些新的床上用品,贴上春联就是。最关键的还是老屋的问题,怎么做工作都是枉然。最后,村支书出面向镇里求情,说暂缓拆掉曾令友的老屋。他还很响地拍了胸脯,保证在检查之前让曾令友先住进新屋,再谋后计。
那天我去杨梅树找贫困户一个一个签字,软磨硬泡,十九户我签了十八户。我告诉村支书,还有一户没签字。村支书说,他知道不签字的是哪一户,交给他去办。我再同村支书一起去的时候,曾令友看也不看我们,在老屋正中烧着火,一同烤着火的还有龙跃海那弱智的弟弟龙跃中。两个老人烤着火,不说话,不理人,唯有柴火独自笑得很旺。村支书蹭下身子贴到曾令友身前,问曾令友到底什么时候搬?他理也不理,不出声,连哼一句半句都没有,双眼半睁半闭,只有柴火旁若无人旺旺地傻笑着。
村支书黑青着脸不说话,临走时说了一句:我想,你还是搬了的好!你眼睛看不见,总有一天会把你家的老木屋烧个干净了事。搬到新屋里,水泥墙砖是断断燃不起来的。
村支书说完就走,这时我看见曾令友半睁半闭的双眼忽又睁开一线缝,一线光亮划过。
果然,第二天,曾令友搬进了新居。搬进新居的他,就在床边的水泥地上旺旺地烧起柴火取暖,屋内窗明几净
那几天,雪下得紧,大家都空闲下来了,扯的扯闲话,打的打牌,无事可干的就盘团火烤着取暖。村支书请假去了珠海他自己办的工厂,我们工作队也好不容易休元旦节假回了邵阳。雪越下越猛,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雪,足有十多厘米,厚的地方近二十厘米,路上行人稀少。高速路上封了车,冰天雪地,寒风刺骨,仿佛另一个世界。
在这样的时刻,我知道村里肯定更冷了。那晚,不知什么原因,我整晚都睡不着,心里有种预感,仿佛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现在看起来,一切都是巧合,一切都是天数,一切都是劫数。
第二天,就知道曾令友在新居烤火起了火,把床上的被子衣服都烧了,好在人没有伤亡。村主任、秘书、妇联主任和镇里领导,踏着厚厚的积雪背着被子、衣物,带着米、油、食品走在通往曾令友家里的路上……
此时,我们工作队和村支书却被冰雪阻隔,不能前去探望,心里甚是愧疚和不安。特别令人痛楚的是秘书发在微信群里的照片,曾令友双眼紧闭,我知道从此后紧闭的还有他的内心。
后来,他天天坐在老屋门口,双眼紧闭。每一次走过,我的内心便痛楚一回。
曾令友的老屋还在,他那深陷的眼眶里,我看不到底。在乡村,有很多看不见和看得见的空洞洞深陷的洞穴,令人迷惑和不解。也许,打开一处洞穴,更重要的是澄清一些疑团,启智乡民的心灵。
好在,现在大家对扶贫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
3
说起赵秀平、赵秀池两弟兄,大家都说真是无法言说。
待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心里就像扎了一根针似的,生生地刺痛,想拔又拔不出来。
那天我们去他们家送慰问品,没联系上他们两兄弟,听村子里的人说他们在打谷子,有一个从小和赵秀池是同学的年轻人自告奋勇地带我们去找。高高的机耕路下面有一丘不大的弯弯水田,水田已被毁得不成样子,因为机耕路边常年掏沙,沙水和泥浆都倾泻到机耕路下他们的水田里。田里不仅被占去三分之一,而且满田都是泥沙,水黄汤汤的,田不像田,禾不像禾,收割不像收割的样子,像是打了一场败仗,丢盔弃甲,惨不忍睹。
喊了几声,只见有应声,却不见人。稻田在机耕路下面,起码有三丈多深。我们走到机耕路边边上,俯下身子去寻找田里的人,终于看到有三个人在田里忙活。由于隔得太远,人影太小,在水田中央,像三株稗草,孤零零的,无助而又迷茫。陪我们来的那个年轻小伙说,看,那就是赵秀池,他的小学同学。他大喊:赵秀池,赵秀池——你还认得我吗?我是你的同学。这个年轻小伙几多兴奋,却不见赵秀池答应,明显地又有几分失落。此时,赵秀池并不在水田中央割稻子,他一个人在水田边上的泥水里玩耍,一只脚扫过来扫过去,在抹平湿湿的泥土上用脚在写字,写了又抹去,再写,再抹,不厌其烦,重复,单调,无趣。他的哥哥正在打谷机上机械地打着谷子,他的大伯母正弯腰默默地在割着稻子,没有人去管他。他仿佛玩在兴头上,一脸的笑,却生硬无趣。
陪我们来的年轻人又喊:赵秀平,赵秀平,你快上来,工作队来看你了!也许是打谷机的声响盖过年轻人的喊声。年轻人下到山坡边边上,双手握成喇叭状,再喊,喊得更急促,更大声。这时,赵秀平好似应了一声,从田中央一脚高一脚低地上了田塍,肩上扛了一大蛇皮袋谷子缓缓地爬上了坡,来到我们身边,一脸笑,身上、腿上、手上都是泥浆,他肩上的谷子仍然在肩,他一只手抓得紧紧的,像抓住自己的命根子一样。我们把过节礼物送给他,他示意我们把礼物放在路边草丛中,仍旧扛了谷子往前走。我们生怕他忘记了,他笑笑,说不要紧,过一下还要再来田里。
这时的赵秀池也已经不在水田中央了,看见哥哥往上爬,他也扛了一蛇皮袋谷子缓缓地爬上了坡。看见我们,像不认得他的同学似的,只是远远地站着,一脸傻笑,怪怪的。陪我们来的年轻人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肩,问还认识他吗,说我们小学是同学呢,还坐过一桌的。
赵秀池仍然不说话,只是傻傻地笑,笑里空洞洞的,没有一点内容,像天空中白白的阳光,呆滞无物。
后来,我知道,赵秀池是村里那个时候唯一考上大学的年轻人,在城里放飞梦想。不想,却陷入了一个传销团伙,被软禁,被洗脑,被打傻,解救出来就成了这个样子,呆若木鸡。他的生活和天空也完全变样,成了一池死水。
好在村里给赵秀平、赵秀池两弟兄办理了兜底保障手续。但是,父母早过世了,大伯母也已经七十多岁了,哥哥赵秀平四十多岁了,弟弟赵秀池也已三十多岁了,家里没一个女人不行。照这样的情况,兄弟俩不可能娶上女人,尽管有安置房,回到家总是冷冰冰的,没有欢声笑语,没有热饭热菜,没有温暖。漫漫长夜里,山里不知心月事,谁晓两个心上秋?
白日里,在山里坐着,在泥里摸爬,在水里玩耍,赵秀池似无喜无忧,仿佛回到了童年。大家经过他的旁边,点点头,又摇摇头,唏嘘不已。
我在想,世上事,尽心知,有些事是兜不了底的。譬如:婚姻、温暖和尊严;譬如:时光、梦想和远方……等等。
4
第一眼见到他,好一个标致的男人!他就是刘业雄,搞了异地搬迁,不久前住上了新房,家里整整齐齐的,看起来还不错。我们入户时,他正在做饭,砧板上的红辣椒切得工工整整,红亮红亮。应声出来,他配合着我们签字、填表,字写得干净利索,又快又好,一身上下也清爽整洁。
村支书介绍,刘业雄修的新房,一半自己住,一半嫂子住。兄长过世了,嫂子去了县城里打工。但他还是锁了东厢房,虽然兄长走了,嫂子随时回来还是原来住的房间。有人告诉他,说嫂子可能在县城里有人了。他说,不管有人没人,嫂子终归是嫂子,一旦回来,总得有住的地方。村子里的人都说,这个刘业雄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我抬头打量刘业雄,看了他签的字,觉得这人应该是有些文化的,怎么就窝在家里呢?也许村支书早已看出了我的疑惑,他说:唉,刘业雄还不是由于讨了一个患精神病的女人,还不是又生了一个患精神病的儿子。就这样,他一辈子守着熬着,从来没动过再娶妻生儿的想法。好多好多好心的人或上门或托人,甚至人家姑娘主动跑来,刘业雄从不动心,一律婉拒。
村支书说,他是走不出来,打不开心结。
我知道,一个人面对每个白天黑夜,刘业雄是在自己的心里打了个死结。
走在路上,我在想,其实解死结的方法,不能着急,仔细找开头,慢慢解就可以了。一定得找刘业雄好好地谈谈心,让他慢慢地走出来,走进新的生活和自由的天空。
突然,我发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现在的帮扶,大多注重于经济上、生活上的,而往往忽略精神层面上的引导和帮扶……
也许,这种帮扶更为重要。也许,那些看不见的帮扶更应该被我们关注。
从刘业雄家里出来,镇党委书记在贫困户赖显宏家里现场办公,要我们马上赶过去。看到赖显宏,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他走起路来,缓慢无神,像往前挪,也像往后移,又是青光眼,很多东西都不看见。据村干部说,原来这个家有3个人,老婆邓里娥2016年去世,女儿赖玲2017年外嫁了,一年到头很少回来过。
这样,赖显宏的家一下子就显得冷冷清清,常常好几天都见不着烟火味。
新修的一间平房,是政府去年帮助改厨改厕的。平房正中架了一个鼎罐,底下有烧烬的冰凉的柴灰,厕所里没有水,窗子也没有装,空荡荡的。平房的地面上有捡来的柴火,平房外面有一个废弃的水泵瘫在那里。老人说水泵用坏了,现在都是担水做饭,提水冲厕所。我问,那怎么不装自来水呢?他说,自己原本有个小水泵,可以抽水的,却没用多久,也坏了。坏了就坏了,自己能提就提点水,反正一个人每天也用不了多少水。末了,他又唉声叹气拍了拍自己拖着的一双腿,说这双腿也太不争气,走起路来就一摇三晃的。
我们一起来的人马上都异口同声地说,给你把水装上,钱不要你管。大家又一起走进平房里,村支书说,厕所里装一个水龙头,厨房外面装一个水龙头,厕所的窗户也给装上。估算一下,也就是一千多元,村里给你出了。村支书边说边就拿出电话,和做工的师傅联系上,要求他们这两天马上就上门搞熨帖了,耽搁不得,越快越好。
赖显宏送我们出门时,他还特意用力地握了我的手一下,我能感觉到他的感谢之情和心里想要说的话。不过,他望了望我,终是没有说话,有些阴郁,有些担心。
走在路上,我又在想,赖显宏尽管当今眼目上的事算是解决了,但是他孤单单的一个人,不知还有多少难题还在等着他……
我想起奶奶生前说过的话:头痛医痛,脚痛医脚,总归不是个好办法。
我在想,乡村的痛,没有切肤的体验,又有谁会去真正地思考?没有真正的思考,是难以找到治病的良策和治本的药方。尤其,现在的乡村还有很多的死结,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开的。但慢慢地解,仔细地找开头,用心地去解,总是可以解开的!
朝远处看,我好像看到有一个人拄了双拐,艰难地从田里一瘸一瘸地走上来了,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田野一片青翠,风过稻花黄。
霎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5
走在路上,我到底还是忍不住,问村支书的微信名为何叫“狂拾叁阎”?村支书嘿嘿笑着,要我猜猜看,我说都猜了三个月了,硬是猜不到一星半点。
他又嘿嘿笑着,说,三个月,也就不远了。哦,难道是三年?就是三年我也猜不出啊!我定定地看着村支书,一脸疑问。
村支书姓刘,是一个致富带头人,原本常年在外办厂,主要生产塑料跑道等文体材料,生意做得活,家产上千万。有个老娘住在村里,他是个孝顺的儿子,一个月要回来一次看娘,呆不上一两天,又要火急火燎地往珠海的厂子里赶。
去年换届,一时半会儿,村里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村支书。有人向镇党委书记推荐他这个能人,一个电话叫回来,镇党委书记当面问他愿不愿意带领大伙脱贫奔小康?他心潮澎湃,一口应承下来,不久就上任了。
有人告诉我,刘书记的爹早年也当过村里的支书,也是一个能干事的人,只是没干几年就过世了,没能带着大家走出苦日子。
硬着头皮上,刘书记说干就干,立马就干,狂干实干。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狂干三年(一届三年),实干三年!于是,选上的当晚他就给自己的微信改名为“狂拾叁阎”。
明白底里,原本谐音,原来如此!
我大呼:“狂拾叁阎”,狂实三年,狂实三年好!
他说,村里这几年,村支两委班子换得勤快,搞得不像样,得好好地拾掇拾掇,狂拾三年,狂实三年!他相信自己,也相信大伙。他是一个不怕难的狠角色,狂干实干是他的法宝。这么多年,他在外面打拼,一个人拾掇得真是不错!
他说,他回到村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他说,他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精准,起码要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乡里乡亲的,都喜欢讲情义,讲势力,讲脸面……他就自己一个人唱黑脸,有些村干部的亲戚投票评上了,他也不通融,一次两次三次去做工作,硬是把不符合条件的人劝退了。村主任的哥哥,就是这种情况。他做通了村主任的工作,终于也做通了村主任哥哥的工作。大伙都说,这个村支书绝不是说说看的,较劲较真得很。
第二件事修通村组公路。没钱也要修,欠账也要修。他说,路不能不修,修路不能等,欠账慢慢还。他说,路是天大的事,路是长远的事,路是致富的翅膀。有了路,各人都能走出自己的一方天地。第三件事是管起村里的钱,开流节支,抠门得很。不该用的坚决不用,能少用的就少用,一分钱当做两分钱用。村干部和扶贫干部加班是常有的事,从来不发加班费,就是吃个盒饭也舍不得。不过,他间三差五掏自己口袋请大伙的客,却是一点儿不吝啬,大方得很。第四件事就是大力发展村里的产业,把一家家种养殖合作社办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村里那些养鸡养牛的、种葡萄种弥猴桃的、栽种茶叶油茶的……都一个个风风火火,脸上流光。
还有第五件第六件第七件事……一下子数也数不过来。去年村里整体脱贫出列,脱贫27户109人,事情繁杂,一件事接着一件事,他不能不在场,不能不带着大家一起狂干实干,他就顾不上自己厂子里的事。把厂子里的事交给了自己的侄儿,但侄儿毕竟手生,隔三差五一定得要他回厂里坐阵,不然震不住。
他当上村支书,厂子就有些照看不上,生意免不了有些下滑。
他最烦的是总有几个人老爱往网上捅他,说些无中生有的事,诋毁他。还有一些人暗中走动串联,想要把他扳下来。他说自己行得正坐得稳,随他们上蹿下跳。耍横耍狠的,他也不怕,有一次他把自己右手的四个指头砸得鲜血直流,那人终是落荒而逃。
他也不唯上,造假作伪的事,形式主义的事,他敢顶着干,撤职也不怕。
他在班子里也很强势,总喜欢自己一个人拿主见,有点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我是第一书记,就对他说,还是要注意,强班子,带队伍,注重团结,体现民主,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弹好钢琴”,拨动全村人……尽管他听着既没赞成也没反对,但我知道他是听到心里去了。
有一阵,刘书记脾气有些急躁,脸色不好看。
有一次,走在路上,我问他后不后悔?他说,男子汉,没有后悔的事!
他说,干一届村支书,付出多少也是值得的。再说,付出了,也是收获了。当然,为乡里乡亲付出,付出多少,都是应该的。
我说,“狂拾叁阎”,你真的只狂干实干三年?
他有些躇踌地说,是的,原来是这样打算的。
我又问:你在乎大家对你的评价吗?
他拍了拍胸脯说:大伙的评价,当然重要;不过,凭良心做事更重要!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我看到他眼睛里的真诚和委屈。
然后,两人默默地走着。过了好一阵,他才说:一直想找个能信任能干事能带着大伙奔前程的人来接手。
搞完乡村脱贫,还有乡村振兴呢!他像是回答我,更像是自言自语。
我说,是呀,这个人不好找呀。“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
我继续说,不光是村支书难找,承接乡村的下一代也是各奔东西,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他没有回答我,陷于沉思。
他一口深一口吸着香烟,望着大山深处,面朝初升的太阳。
烟雾袅袅中,黎明的霞光从山峦中静静地浮出来,从微白、淡紫、浅蓝,瞬间幻化成橙红、桔红。
我们往梅树山上走去,四野青翠欲滴,春色愈来愈深了。
6
我们去赖必培家,给他带了年画、挂历、星书和通书,还带了几本关于乡村振兴的新书。有人说他是个文化人,他更喜欢和在意这些东西。我问,他怎么也是贫困户?村妇联主任说,他的人缘关系好,加上他们两个老人年纪也比较大,还在田里地里操劳,于是大家一评就把他评成了贫困户。乡里乡亲的,大伙当面都说当评,一个组总要评一户,不评赖必培评谁呢?
赖必培是一个老高中生,逢人一脸笑。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要请他去写字,写对联,作祭文,掌事。他一到,字一写,要喜气喜气马上到来,要悲痛悲痛的气氛也会立马弥漫开了。
进门,院坪里的晒谷坪竹席上有花生、红辣椒、甜玉米,赖必培笑着出来相迎。他喊我们在晒席上随便拿花生和玉米,我们也不客气,自己去拿,开心地吃着。村妇联主任还把门边的甜甘蔗拿过来,一人一长节,要我们工作队的人尝尝鲜,说别看是毛甘蔗,甜得要命。赖必培赶忙作证,是甜,但要小心,不要割着你们的嫩嘴巴,我可不负责呢。我们忙捂着嘴巴笑,吃得更开心。大伙吃了花生,吃了玉米,吃了甜甘蔗,气氛更好。然后,就说正事,就说根据上面的政策,易地搬迁这房子,平顶上还要盖上瓦,验收合格后按每平方米120元结算到位。
赖必培就笑,那敢情好,政府真是好,想得细,想得全,想得周到,怕老百姓冻着、饿着、晒着、热着,怕吃水不安全,怕住房不安全,刮风漏雨,怕义务教育不到位,一个都不能少……真是想得要多周全就有多周全!
在堂屋里,我看见有两副红红的对联:仁义堂中无限乐,芝兰室内有余香;修新屋搭帮共产党,建华厦感谢习主席。对联又宽又长,字写得遒劲有力。赖必培站在一旁,笑着自谦地说:涂鸦,献丑!
再去看他家的厨房,冰箱、抽油烟机、饮水机等一应俱全,还有新式的厨房组柜和省柴灶。卫生间里,是吉利牌的全自动洗衣机,悬挂式的洗浴池和浴镜,还有抽水马桶,四壁都贴了壁立瓷砖,崭崭新。
快八十岁的赖必培,在家里的只有一个老伴,他的儿子媳妇孙儿孙女都在外面打工。他和老伴在家里,种田耕地,田里地里,也不闲着。晚上的时候,他喜欢去村里的图书室借书看,尤其对关于乡村和农俗文化的书特别爱好。
静下来的时候,爱看书的赖必培对乡村的前生今生,还有未来,不免有些忧思。忧思归忧思,可是没有几个人愿意听他的大道理。碰上了,大伙都说忙,或者远远地看到他就躲开了。尤其是村子里的年轻人长年在外,一年到头难逮着几个人听他说道。
这样,他就常常一个人在村里头自言自语:人嘛,光有吃有穿、有车有房,没有文化,还不是一具皮囊!一个地方再怎么富裕,如果不讲礼仪,不讲情义,不讲诚信,不讲信仰,不讲善心,不讲传承,没有文化,终将成为一团散沙,终将成为一团乱相……社会主义新农村,绝对不是这样的!
每次,我听到赖必培老人自言自语,总在不远不近处停下脚步。
村子里有红白喜事时,大伙才记起赖必培。这时,他的一手好字排上用场,礼仪上的事也都是他在主持,事无巨细,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妥妥当当。
可是,他最焦心的是白喜事。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每逢村里有人过世,村里头连抬棺材上山的劳动力都没有几个,要去外面请人,工钱开得天价一般。他急得直跺脚,遥望无边的青山,青山无语。
一到春节,村子里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贴了他手写的春联,龙飞蛇舞,句雕风月。红火火的日子,春光无边。这个时候,是他最高兴也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刻。他写的春联,有“江山千古秀,祖国万年春”,有“新路新房新景象,新风新貌新农村”,有“党重三农铺就小康路,民勤四季敲开富裕门”,有“家和万事皆兴旺,人勤五谷全丰登”,有“耕为立命之本,读是修身之策”,等等。每一家春联,他从不重样。都是同一个福字,却有百十种写法;都是喜庆的春联,却各是各家的喜庆。大伙都赞说赖必培老先生,一个个竖起大拇指。
他最幸福的时刻,是踱着方步,一户一户门前去检阅,去欣赏。他抚着山羊小白胡子,看一眼,点一下头,再看一眼,又点一下头,整个村庄都仿佛装在他的心中。
心中的喜,心中的忧郁,心中的幸福,心中的悲愁,心中的希望,心中的思索……一刹时,一切都在青山绿水间飞扬。

作者简介
周伟,1971年生,现居湖南邵阳。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著有散文集《乡村书》《乡间词韵》《一个字的故乡》等,儿童文学作品集《一地阳光》《看见的日子》,小说集《白水点灯》,长篇小说《平安无事》。作品被《新华文摘》《中华文学选刊》《作家文摘》《小说选刊》《散文选刊》《儿童文学选刊》《读者》等转载和中央电视台选播,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等两百余种选本和中学语文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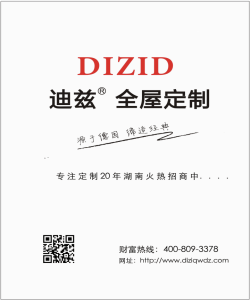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