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的茶缸
随身的茶缸
文/刘宏阳
搪瓷茶杯,因为较大,又称茶缸子。
最近,当我端起茶缸喝茶的时候,几次想起了很多年前我曾用过的一个搪瓷茶缸,由此,脑海中也翻出了一段与那个茶缸有关的陈年往事。

▲刘宏阳老先生近照。
1949年,我在长沙修业农校读书;同年8月5日,陈明仁宣布起义,长沙和平解放,解放军列队进城;9月我参军了,先是在军大湖南分校,年底转工兵学校;1951年1月,我被分配到驻长沙的工兵十八团器材供应股。春节后,部队赴衡阳执行任务。

当时,我有个本家族的姐姐,在长沙市某机关工作,得知我要离开长沙,想买点什么作为送行的礼物,问我缺什么,我想了一阵说:“选个喝水的茶杯吧!”她说,要得要得。边走边聊,在中山路国货陈列馆买了个白色的“洋瓷缸子”。
去衡阳茶山坳后不久,任务突变,赴北上抗美援朝。

在列车上,就显露了这个茶缸的实用价值。军列,不是客车箱,是闷罐车皮,要坐人,放枪支弹药、工具器材。吃饭、洗漱,都不是在列车上,而是要下车到某个指定地点才能完成。
列车还没到站,有关部门(或者是先遣人员,不清楚)已将饭菜做好,一排排的行军锅灶摆在了站台上。
下车用餐,或将饭菜搬到列车上吃。搪瓷小碗倒是每人一个,但拿来打开水、喝汤就有点不好办。太小太浅盛不了多少且不说,泼泼撒撒,端着还烫手。大家见我用较深的茶缸,稳稳当当,干脆利落,很是羡慕,尤其是从军大分配来的女文化教员或宣传队员,甚至想要强行夺走。
车出山海关,到了东北地区,吃了两次猪肉炖粉条,一个长柄大勺,直插行军锅底,勺大碗小,粉条又不短,倒在碗里的,还没有掉在碗外的多,气死人。
车到安东,稍作停留,整装待发,步行奔赴目的地。黄昏过后,踏上鸭绿江大桥,开始了夜行军。虽不是急行军,但战士们行军打仗习惯了,一踏上征途,小老虎一样迈开坚实的步伐,行进的速度却也不慢,在天亮前,一定要赶到宿营地,白天隐蔽,敌机一旦发现目标,肯定会轰炸。
行军途中也要喝水,喝水时,不可能等到喝完了再走,得一边喝,两脚还要大步流星往前赶,稍慢一点,就会拉开一大截距离,后面的人直催:“跟上,跟上”。要喝水,当然比不上我这个用茶缸的。就算你有个军用水壶,对着嘴喝,磕磕碰碰,撞击牙齿,也喝不了几口。长途行军很辛苦,要体力,要久经锻炼,这对于参军不久的人,尤其是女兵们,很难承受。第一晚过半夜后,几乎全数爬上了收容车。

在行军途中,这个茶缸,不单是吃饭、喝水,连打水、洗脸、漱口也用得着,方便极了,真是人见人爱。几个战友,要与我以物易物,有人提出用香肠换,有人说用罐头换,我一概婉拒。
于是,在往后的日子里,我腰上经常栓着个白色茶缸。
我团基本是在西线战场执行任务,地域宽广,兵力分散,有修建阵地的,有维护公路桥梁的。哪里有任务,哪里就要供应器材。几年来,我就带着这个茶缸,沿着西线,从鸭绿江至板门店来回穿梭。人总是要吃饭喝水、洗脸漱口的。有人说我身上3件宝:一支51式手枪、一个挎包、一个茶缸。这3件宝,跟着我艰苦欢乐与共。我记不清多少次险情擦肩而过,严冬冻僵,战友抱着我从车上下来,烧水温手足,捂棉被;天雨一身泥,房东大妈抢着替我洗衣服。
我团一营从永柔出发,去东海岸的元山地区修筑炮阵地,途中经过阳德。阳德有个兵站,我要去兵站领器材,随车前往,在阳德下车,独自去兵站,等第二天晚上车辆返回时将器材拉走。
阳德附近有一险要地段,两边是山,两山之间有一条公路、一条铁路,形成了东西交通的一道关卡,美国鬼子用轰炸将它封锁,每个昼夜,敌机光顾无数次。
在此,车队遭袭击了。前面数起火花,几声爆炸。
我坐在驾驶室,左边一个司机,右边一个副驾驶。我见车前十多米处耀眼的白光一闪,一声巨响。
山头的探照灯亮了,一道道光柱,在空中扫来扫去;高射炮也怒吼了,天上一片火海,地面一片火海(这种场景,无论白天黑夜,也无论前方与后方,时刻出现,不足为奇)。有伤亡,司机负重伤,副驾驶牺牲。真是死神贴着皮肤,从我的两侧挤过去了,只有数处轻伤,微不足道的。车上的25名战士伤亡过半,前后车辆也有损伤,但极少。营部有一中心文化教员,湘潭青年,牺牲后惨不忍睹,一块弹片,削了他半个脑袋。
我与大家一道救护伤员,撕开一个个急救包,包扎伤口,伤员的鲜血和我自己流出的血液,将衣服弄得血迹斑斑。
收拾现场后,车队继续出发,很快就来到了去兵站的岔路口,我独自下车。在月色下,见有一条水沟,水面离地面较低,我取下茶缸,蹲在沟边,尽量弯着身子,很吃力地一次次打水洗脸漱口,擦衣服上的块块血迹,整理一番,花了半小时光景,才能在人前不显得那么窝囊,不会吓着人。
兵站,是不提供食宿的,只好在一民房休息打个盹。此刻,我已经非常疲乏。
早餐就简,在茶缸里冲泡了两块压缩饼干,其他两顿,在房主人家做。
我随身携带有两节香肠和一块咸萝卜,没舍得吃,为报答房东,把香肠留了下来。
第二天晚上,汽车来了,装车后还没有离开兵站,又遭到轰炸,牺牲了一名司机。
这两个晚上加一个白天,茶缸在手中转来转去不知多少次,解决了不少问题,我真不能没有它。可惜的是,它后来丢失了。
(刘宏阳,90岁,写于长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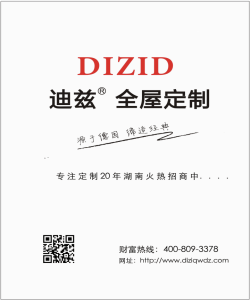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