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邦散文赏析 ▎歉疚

——值此庆祝教师节之际,谨以此文献给为孩子们的成长辛勤工作、默默奉献的老师们!
歉 疚
文/刘克邦
童年时期我与老师的一段往事,让我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那一年,我还小,什么事都不懂,什么事又都懂一点。
我父母亲都是老师,父亲早年因“不安分”被打成“右派”遣送回了遥远的湘乡农村老家,母亲因遭受精神打击积劳成疾也离世而去。
在母亲同事们的照料下,我在那所偏僻的山区小学过着“孤儿”般的生活。
那所小学是全公社唯一的一所完全小学,学校里有十几位老师,除了几位有家属的老师外,其他老师都要和十几位寄宿同学在一个食堂里吃饭。
三年“苦日子”刚过,生活还没有好的转变,餐桌上每人除了一小钵子米饭外,每天不是白菜就是萝卜,看不到多少油星,一个月也难得开一次荤。
我年幼无知,好动好玩,又要上课读书,消耗量大,又是长身体的时候,这点饭菜与身体所需相差甚远,饥饿袭来,经常感觉到心发慌、头发晕,走路打撇脚,上课没精神。
我一反常态的反应,被一位细心的老师注意到了。
他姓吴,名希伯,是我母亲的同事,也是我的算术和音乐老师。他四十开外,方正脸,黑皮肤,身材略显瘦小,但两眼炯炯有神,性格开朗,乐观得很,待同学亲切和善,大家都十分喜欢他。
一天,下课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一边:“克邦,你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好吗?”我没做声,转身走了。
我知道,他也挺不容易的,他的爱人我叫师娘是一家庭妇女,没有工作,还有两个孩子,一个比我大,初中毕业后一直呆在家里,一个与我相当,是我的同班同学,也正是吃长饭的时候,一家四口全靠老师一个人工资养活,日子够艰难的了。
吃晚饭的时候,我依然向食堂走去,吴老师的儿子、我的同班同学在食堂门口拦住了我,说他爸爸妈妈非要我去他家不可。推托不了,只好跟随着到了他们家。
他们所谓的家,就在学校里两间教室中间,一大一小一前一后两间小屋,估计最多二十来个平方米,全家大小四口吃饭睡觉都挤在这里。算是特殊照顾,学校允许他家在教室顶东头搭了一间小杂屋做厨房。
在我的记忆里,他家寒碜得很,桌子是公家的,床铺也是公家的,除此之外,没有一件像样和值钱的东西。
进了门,一见面,老师就埋怨起我来了,“说好了要你过来的,怎么就不听老师的话?”师母也边忙边热情地招呼我:“快坐!快坐!好遭孽的冒娘崽!”其实他家哪有坐的地方,我犹豫了一下,只好屁股一贴,顺势坐到床沿上。
一会儿工夫,师母把饭菜做好了,一一端了上来。
我一看,好家伙!像过年一样,一大碗晶莹剔透的红烧肉,一盆鲜嫩肥美的清炖鸡,外加一炉锅白花花香喷喷的大米饭,好久没见过如此丰盛的美味了,我差点没掉口水下来。
老师把筷子递给我,“看你好久没开荤了,这是你师母特地为你准备的,你就放开吃吧!”
师母像待亲儿子一般,给我盛了一大碗白米饭,并一个劲地夹肉夹鸡往我碗里送。我含着泪,咀嚼着这人间的香甜和温暖.....
以后,老师接三间四地总把我叫到他家去打餐“牙祭”。
听我那同学说,我每次去他家之前,他妈妈都要叮嘱他们兄弟俩,说我母亲不在了,父亲一下子又联系不上,小小年纪,怪可怜的,要他们少抻点筷子,让着我多吃一点。
听到此话,我哭了!
没过多久,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这个偏远山区的小学校也不甘落后,不分老师学生,也不分男女老少,不停地开会、学习、报告、演讲,先是批判“三家村”,慢慢地风向一转,开始在学校老师中寻找批斗对象了。
大家发现,吴老师是富农出身,是学校里家庭成份最差的人,想当然也一定是思想和立场最反动的人,便把他“揪”了出来,集中火力批斗起来。
一时间,“坚决批倒批臭资产阶级分子吴希伯!”“吴希伯,你只有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才是你唯一的出路!”“不打倒吴希伯,誓不罢休!”之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整个校区。
我惊愕!我疑惑!吴老师是好人呀!
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反党、反社会呢?我不明就里,也不知如何是好。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随着革命斗争的一步步深入,“一贯向学生灌输读书至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毒害青少年呀!”“发泄不满情绪反党反社会呀!”“教学生唱庸俗小调靡靡之音,妄图以资产阶级思想占领我文化阵地呀”......一顶顶“帽子”扣在老师的头上。
不能解释,更不允许争辩,吴老师只能忍气吞声、低头做人。
一天,学校革委会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从革命的大道理到如何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地富反坏分子划清界线,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他话锋一转,“听说你经常去吴老师家吃饭?”
“是的,他很关心我。”我一脸惊恐,胆怯地望着他!
“关心你?你也太幼稚了点。他这是在拉拢腐朽你呀!你可要站稳立场,与他划清界限啊!”他冷笑起来。
看我没做声,他接着说:“明天学校要开一个声势浩大的批斗会,所有老师、学生和家属都参加,主要是批斗吴希伯。交给你一个任务,你上台发一个言,就揭露吴希伯两个问题,一个是他经常吃肉吃鸡生活奢侈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个是他对你施小恩小惠拉拢腐蚀青少年房妄想复辟翻天。”
天啦!这是要我说什么呀!我脑袋瓜子“轰”地一下涨得老大,刚要张嘴说点什么,他不由分说,手一扬,“就这样定了,这是革委会的决定。”
第二天,吴老师被挂上黑牌子,戴上高帽子,低着头,躬着腰,站在台上,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接受批斗。按照预先的安排,老师、学生一个个上台,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揭露和批斗他的一桩桩“罪行”。
我至今仍不明白 ,鬼使神差,当时,不知道我是怎么上台去的,也不知道我在台上说了些什么,更不知道我又是怎么下来的,脑子一片空白,像一具没有情感和灵魂的木偶,机械地、照本宣科地“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
我就像一个偷了别人东西的贼,始终低着头,红着脸,不敢看老师一眼。
惭愧呀!内疚啊!我为自己的所为难过得要死。
自从那次批斗会以后,我再也不敢去老师家去了,老师也不敢再喊我去他家吃饭了。
后来,我被父亲接到了湘乡,在农村摸爬滚打,度过了“十年浩劫”,在恢复高考时才重新步入学习深造的殿堂。
我也曾经几次回到那个伴我度过童年时代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但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完小已升为了中学,且迁到了新的地方,更不见吴老师的踪影。
经多方打听,有人告诉我,吴老师自那次被批斗以后,精神恍惚,卧病不起,不久就携全家回老家去了,具体在什么地方搞不清楚。
我曾多处寻找,想向他表白点什么,但徒劳无功,始终未能与他相见。
50多年了,这件事一直无法从我心中抹去,像一块巨石沉重地压在我灵魂深处......
作者简介
刘克邦,湖南湘乡人,文创一级,高级会计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省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天津文学》《山西文学》《安徽文学》《散文海外版》《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芙蓉》《湘江文艺》《湖南文学》和《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财经报》《湖南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200多篇;出版散文集《金秋的礼物》《清晨的感动》《自然抵达》《心有彼岸》4部;获全国第六届冰心散文奖,湖南省第四届毛泽东文学奖,财政部文学征文一等奖,中国作家杂志社征文一等奖,长沙市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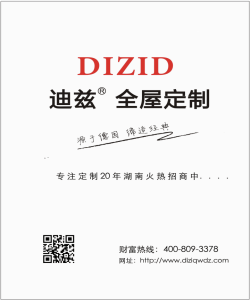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