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邦|《邻居刘四爹》
邻居刘四爹
刘克邦
那是一个缺吃少穿的年代。
“老大哥”援建工厂,我家从原址迁出,移建到一处新的地方。这里房屋稀少,仅在百米开外,才有一户人家,也算是最近的邻居了。
邻居主人叫刘四爹。虽然我们都姓刘,但无亲缘关系,之前也不是很熟。我们虽然是邻居,且为远近数百米间唯一的邻居,但我们都是拆迁户,来自于不同的生产队,我家属一队,他家属三队,在各自的队上出工、分谷子,因而交往不多,关系不亲也不疏。
刘四爹一家六口,上有年迈的母亲,下有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妻子患有痨病,长年卧床不起,咳嗽起来没有个完,应该说,生活过得挺艰难的。但他吃得苦,精于盘算,每天除了在生产队出工外,一回家要不就提把锄头或挑担粪桶直奔自留地里忙活起来,把个菜园子盘弄得井井有条、活色生香;要不就是拖到凳子坐下来,手不停歇地搓草绳、打草鞋,积攒起来卖出去,赚几个小钱,小日子也还算是过得去。
令人称奇的是,他的菜园子里除了长满了全家餐桌上必需的萝卜、白菜、豆角、南瓜、冬瓜等蔬菜外,还有其他农家极少栽种的西瓜、凉薯、花生、甘蔗等罕见的作物。
这些作物虽然经济价值高,收成后可以挑到附近厂区兜售,或多或少换得到一些家中缺少的纸票子、银角子,但种植技术要求高,人工、肥料投入大,还要祈求老天爷帮忙,少从中作梗,否则,会事与愿违,收效甚微,甚至血本无归,乡民们大都望而生畏,不敢涉及。
也许是家境所迫,刘四爹却偏不信邪,我行我素,一头扎进菜园子,下种、移栽、浇水、施肥、松土、除草、整枝……像侍奉孩子般的盘弄起这些作物来,魔幻般地叫它们一株株破土而出,枝繁叶茂,生出满地的财喜来。
那个清晨的所为,让我无地从容,羞愧了一辈子!
七月,对于农村来说,是一年中最繁忙、最难熬的季节。天上挂着比火盆还烧得旺的太阳,直烤得路面直冒青烟,树叶卷了,野草黄了,地里的瓜菜也蔫了,横卧在屋檐下的小狗小猫们呼哧呼哧直喘粗气。为了不误农时,也为了生存,在生产队的严格管理下,社员们每天起早摸黑,弯腰勾背,咬紧牙关,顶住“火炉”的残暴烘烤,抓紧时机将田里稻谷收割上来,将晚稻抢插下去。
那年,我12岁,年纪虽小,生计所迫,也卷入到这场抢收抢插的恶战中。扯秧,插秧,杀禾,看牛,割草,一天劳作十多个小时,忍受着难以想象的饥饿和劳累,像水牛一样背负着沉重的犁轭在酷暑中、泥潭里挣扎与喘息。每天收工回家,两腹空空,饥渴难耐,经过刘四爹那片枝繁叶茂、绿阴如盖的凉薯地,想象着那地底下生长的一个个水泱泱、脆甜爽口的凉薯时,就垂涎三尺,有一种欲罢不能极想品尝一口的冲动。
人心底下,拴着魔鬼,稍不留神,它就蹦了出来。我终于忍不住了,起了贼心。
一天凌晨,天还没有亮,我起了个大早床,悄无声息,蹑手蹑脚,低着头,勾着腰,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来到那片凉薯地。第一次做贼,我紧张极了,瞪大眼睛四处搜索,确信没有人时,才弯下腰来,摸到一株凉薯藤,抓住贴近根部的茎杆,一个骑马桩,铆足劲就往上拔。殊不知,那凉薯倔强得很,根本不吃我那一套,任凭你使出吃奶的劲来,深扎在土里纹丝不动。我左一下,右一下,变换着方式拔,怎么也拔不出。一株不行,换一株再拔,还是不行。连续拔了好几株,力气用尽了,不是揪断了藤条,就是剐脱了䕨茎皮,除了一手黏糊糊的䕨汁和湿漉漉藤皮碎屑外,连个凉薯影子也没见到。
我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坐在地上,沮丧极了。眼看天快亮了,我忙活了一阵子,仍两手空空,好不容易架起了这个势,实在不愿就此善罢甘休。正待起身再干时,“谁?”一声喝问,声如雷霆,不远处一个身影在晃动。
哇,是刘四爹!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情知不妙,转身就跑。他肯定看清了是我,追了几步,没有再追,在后面冲着我大喊:“我告诉你家大人!”
我害怕极了,这下子完了,全完了!那时候,在农村虽然物资匮乏,但人心淳朴,偷东西可是最让人痛恨遭千人指万人骂的行为。平日里,父亲对我要求十分严格,绝不允许我去干那些损人利己的事情,如果知道了我去偷邻居家地里的凉薯了,肯定免不了一顿臭骂和毒打。我又是一个爱面子的人,此事一旦传开出去,村里村外人前人后我还抬得起头吗?
我低着头,怀着恐惧的心情回到家中。父亲见到我,劈头就问:“一大清早去哪儿了?”“扯秧去了。”我撒了一个谎。“刚才刘四爹来了,找你有事吗?”父亲用疑惑的眼光瞟了我一个眼。“没,没,没什么事!”我强作镇定,生怕露出什么破绽来。从父亲的语气中,我已知道,刘四爹来过我家,但没有提及我偷他家凉薯的事,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落下来。
一天,两天,三天……我像一只惊弓之鸟,竖起耳朵听人家说些什么,仔细观察别人的眼色和神情,心里面不停地忏悔着,祈祷着:我再也不去偷东西了,千万别有人叫我贼呀!幸运的是,刘四爹网开一面,未将我的“丑行”散布出去,我担心的可怕的结局始终没有出现。
我无地从容,悔恨不已,觉得很对不起刘四爹,老远老远躲着他。
“双抢”进入了最火热最激烈的阶段,队里收上来的新谷子还在晒谷坪里,要等晒干车净后才分到每个家庭。而这时,我家的米缸已见了底,每天的劳动强度只增不减,不吃饭哪有力气去干活?无米下锅,祖母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
父亲手拿簸箕,把我叫过去,“去,到刘四爹家借几升米来!”一听到要到刘四爹家去借米,我心里咯噔一下,扭转身子,躲到一边,显然不愿去。怎么了?父亲不明就里,平日里言听计从的儿子,今天竟违抗起他的“命令”来。“家里没米了,你好生跟四爹说,就借几升,哪怕一升也行,度过这几天荒,待队上分了新谷子,马上就还。”他追过来,连哄带劝。“我不去!”想起凉薯地里的事,我心有余悸。“你敢不去!”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父亲怒目相向,厉声呵斥。“双抢”时节,青黄不接,谁家的粮食都不多了,虽说是邻居,但要向人家借米,还真是一件难于启齿的事。大人爱面子,只好把小孩推在前面。
走向邻居家的路很近,但对我来说,好难好难,太长太长。我磨磨蹭蹭,走一步,停一下,再走一步,再停一下,不到一百米的距离,不知走了好长的时间。我一边走,一边想,我怎么有脸面见四爹,我该怎么向他家说呀!
好不容易来到刘四爹家,我站在窗台下,犹豫了好久,硬是不敢跨进那扇门。正徘徊之际,一阵咳嗽声传来,刘四娘站在了我的面前。“克邦,有阿么事?”我一脸通红,吞吞吐吐,“我——我——我家没米了!”我心虚得很,偷凉薯的事,四娘肯定知道,恨不得一下子钻到地底下。“我家的米也不多了。”见我拿只簸箕,她明白我的来意,迟疑了一下,很快就转变了口气,“没关系,匀一点给你!”她抢过我的簸箕,转身就进屋去了。
我感激涕零,连声谢谢都忘了说,接过小半簸箕米就走。刚走出几步,后面一声“等一下”,是四爹的声音,吓了我一大跳。拐了场,那天的事,他还没有跟我“算账”的。我止住了脚步,站在那里一动都不敢动,心里怦怦直跳,等待着一场暴风骤雨的来临。
他追上来,端着满满的一升米,“哗啦”一下倒进我的簸箕里,“你四娘量(用升子装)少了,不够你家吃两天。”声音很小,但亲切温馨,如洪钟般敲得我的心灵铮铮作响。
我哭了!捧着沉甸甸的簸箕,低着头走了,始终不敢回头望他一眼!
作者简介
刘克邦,文创一级,高级会计师,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省散文学会名誉会长;出版散文集《金秋的礼物》《清晨的感动》《自然抵达》《心有彼岸》,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天津文学》《散文百家》《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山西文学》《芙蓉》《湘江文艺》《湖南文学》和《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财经报》《湖南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200多篇;获财政部征文一等奖、全国第六届冰心散文奖、湖南省第四届毛泽东文学奖等奖项。
来源:鲁茅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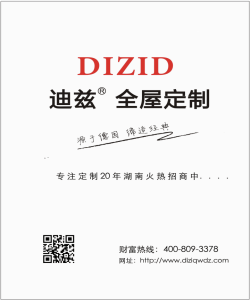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