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精选 ▎故 园 小 聚 (文/范精华)
故 园 小 聚
文/ 范精华
功 勋 鸡
我老家在洞庭湖区,多养鸡。家里有一只黄色羽毛的母鸡,是前年初夏买回的,那次同来的有六只,每只均在三斤左右。至今,“六鸡小队”就只剩它了,其余五只命多乖舛:两只被邻家的狗咬死,尽管那狗被主人处以重刑,挨了几木棒,但鸡死不能复生;一只从渠边觅食掉下陡磡淹毙,属于“工亡”;一只酷暑下完蛋后突然倒地不起,算是“难产”而死,鞠躬尽瘁了;一只送给产妇补身子,早就“灰飞湮灭”。
这只命大的母鸡创造了辉煌业绩:15个月内,以两天连下两个蛋,歇一天不下的节奏,如计算机一样准确,下了300多个蛋。它下的蛋比别的鸡下的蛋要大,八个有一斤,每个蛋可卖两块钱。也就是说,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它创造了六百多元的价值。
但从今年一月开始,它不下蛋了,尾巴开始掉毛,渐渐可以看到红彤彤的屁股;脖子上的毛日渐稀疏,通红的脖子犹如一根火腿肠;胸前的毛也有一大块没了,露出红色的胸脯,仿佛小孩子胸前戴着红兜肚。它的身形比原来缩小了一半,瘦了,憔悴了,杂乱的羽毛毫无光泽,胡乱张开,在春风中抖动,丑陋不堪。因为它生的蛋太多了,生得太苦,奉献太多而损坏了自己的身子。
一只母鸡,不能下蛋是很危险的。弟弟说,它现在白吃食,又近年关,不如宰了过年。全家人一致反对,这鸡不能杀,因为它功勋卓著,并形成决议:让它活到自然老死的那一天。同时,通过另一项决议,宰掉另一只母鸡,并历数它的罪状:强占鸡窝不下蛋还经常高唱“个个大”,欺骗主人;鸡冠高耸鲜亮不但毫无用处,还是放荡的标志;体形大却争强好胜,经常啄咬其它母鸡甚至公鸡,抢夺食物,破坏团结,鸡品很坏;民愤尤其大的是,它常窜进厨房拉屎。
获得终身豁免不挨刀的母鸡也没见它闲着,就在当下,它也比其它鸡要“奔食”些,就是更会寻找到吃的。一大早,它从鸡笼里出来,就屁颠儿独自去附近的田里、屋场觅食,白日里很少回家,傍晚归笼也晚些。常见它将脑袋挨着石头左右摆动,将喙在石头上反复打磨,就像人磨刀一样,使之锋利,便于捉到虫子等“活食”。不过,它要是饿了,就会毫不客气地啄主人的裤脚一直不松口,提示你该给它喂食了。经过两个多月的“调养”,它似乎恢复了元气,鸡冠竖起来,抖动着,又红又艳,还唱起了歌,但毛色和体形还是大不如从前。
没想到,这几天它又下蛋了,仍是两天连生两个,间隔一天不生的节奏。两只鸡命运完全不同,真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哦。
酸 橙 树
我家房子坐北朝南,房前有一个很大的院坪。院坪的南面,是一个长方形的菜园,与房子平行。在院坪紧挨菜园围栏的正中孤独地长着一株酸橙(又名臭皮柑)树,约两层楼高,枝叶繁密,四季常绿,夏日我们坐树下乘凉,竟不见漏下一缕阳光。它的主干敦实粗壮,带浅绿色,上面有弯弯曲曲的竖条纹,更增添了阳刚之气和苍桑感。
这株树是有故事的。40多年前,生产队常从长沙收集阴沟垃圾作种棉的基肥。我在一株棉苗边发现了这棵“橘树苗”,估计是从城市垃圾中带来的,便将它连同周围的泥土撬起栽种在自家菜园篱笆边,长大后才发现是一株酸橙树。
酸橙树本来长得慢,因在菜土边,水肥,阳光充足,三四年间它就长到一层楼高,伸出的枝桠将菜土的阳光遮去不少,惹得父亲不高兴了,将其枝条砍去大半,只允许伸向院坪的枝桠自由生长。
春天一到,满树繁花,白色小朵,香气袭人,连离我家半里路的南边庄户人家,都跑来跟我父亲说,这株树好香哦,北风一吹,都闻得醉了。它结的果实也特多,大片翠绿中露出簇簇金黄,一到深秋,将枝桠都压弯了。
只是,酸橙果实能酸掉大牙,那时却不愁没人吃。邻居的小屁孩经常像猴子般溜到树上,摘了往地上扔,另有小伙伴拾起来用衣襟兜着,再悄悄一齐溜到屋角后有滋有味地啃。我家也没怎么管这事,只提醒,小心点摔烂了屁股没得赔哦。后来孩子们便大呼小叫而来,如同攻打城堡的游击队,勇敢而顽强,收获满满才凯旋而去。有一天,我二妹透过叶隙隐隐见树丛中有红色的东西在挪动,走到树下仔细一瞧,大吃一惊!邻队的一个孕妇不知什么时候爬到树上,正骑在树杈上慢悠悠地吃酸橙呢。二妹赶忙将她扶下树,又摘了些酸橙,倒了茶,搬来椅子让其坐下,好好侍侯,惟恐生出意外担当不起。及至初冬,满树的果子,便荡然无存了。
可到如今,它孤零零地存在,没人欣赏,也无人打扰,顶多也就遮个荫,勉强当做一株绿化树。每到深冬,从树上掉下来的酸橙又大又红,滚满一地,还得花精力收拾进垃圾箱。看来,有用和无用都是相对的,也总是在变化着的。
石 拱 桥
我故居的位置,相当于汉字“可”中的口字,那一“竖”是条乡村公路,直通湘江大堤;一“横”则是一条大渠道,称南干渠,是这个垸子的主要排水通道。自然地,“竖”与“横”的衔接处,是一座石拱桥。
石拱桥建于1965年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年代,至今也没有名称,但其作用可不小。那些年月,每当旭日初升,最先从它上面走过的是稚气未脱的村童,他们要去学校;夕阳西下,牵牛晚归的是耕耘回家的犁把式。上世纪70年代,人们从桥上走过,脚步匆匆;80年代,骑着单车而过,铃声叮叮;90年代从桥上行,摩托轰鸣;新世纪从桥上驶过,轿车滴滴。
石拱桥,犹如一本乡村生活的记录簿。
小桥流水,历来浪漫故事多,石拱桥也未例外。有一天下着小雨,有个帅哥骑自行车过桥,恰好桥那边有一个打着雨伞的美丽姑娘款款而来,帅哥见到姑娘半遮半掩的姿态迷人,春心触动之际走神儿了,小桥又没有护栏,连车带人“扑通”一声栽入桥下。姑娘见状,慌忙从桥边绕坡而下救人,未想步履不稳摔了个素面朝天,浑身沾满烂泥。她也顾不上这些,伸出勾把伞去搭救小伙子。这时,住渠道两边的人都赶过来帮忙,三下两下,便将小伙子和他的单车一起捞了上来。人们以为是一对恋人,便开始调侃:“小伙子,骑车搭个妹砣要小心点哦。”“这姑娘好漂亮,小伙子好福气!”说得那姑娘面红耳赤,伞也忘记拿,就悄悄地离开了。
后来,小伙子为了还这把伞,也为了表示感谢,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姑娘家。再后来,两人结成伉俪。故事和石拱桥一样有点老套,却又有点迷人。
人生的际遇中,偶然因素能成就多少事儿?你知,我也知。
守 队 屋
分田到户之前的生产队,都是有队屋的,就是生产队储存稻谷及棉花、玉米种子,收藏犁耙、水车等农具的屋子。
队屋晚上要人值守,以防盗窃。有一小房间备有床和棉被及蚊帐等物,供值守社员歇息。值守人需要保持相应的机警,必要时还要起床巡查。守队屋,是社员们轮流来的,必须是两人,守一夜,每人给工分两分。我喜欢守队屋,能获得一种新奇感,还可以得工分,队屋里弥漫的稻谷的清香也让人受用。
队屋盛产老鼠。谷物盈仓,鼠类应不会争斗,可常在夜间上演全武行,忽而哗啦大响,忽而吱吱怪叫,有时竟如一筐卵石倾地,轰然一声响后复有滚动之余韵,让人好不烦恼。后采用高人建议,在大门边脚处留一小洞供猫出入,队屋果然宁静许多。
一个秋夜,细雨纷飞,是我和哥们祥宝值守。祥宝蛮谨慎的,也负责。晚上八点多,他先我一会到队屋。在我离队屋还有几十步时,突然听到他大叫一声“哎哟”,我惊问怎么了?他不回答,只顾干嚎。我以为他遇到了盗贼,慌乱中揿亮手电筒跑了过去,才知他被竹夹子夹了。我们这里有用竹夹子捕捉黄鼠狼的习惯,装夹子的人一般是在天断黑时设置,以免让人看见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也可以不告诉相关的人。那晚队里配的手电筒是我拿着,祥宝到后依稀发现大门边脚的洞口放着什么东西,便顺手一摸,中招了。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扳开夹子上的弹簧,他的手背被夹青一大块,肿了半个月。
由是想起,队屋复归宁静,还有黄鼠狼的功劳。第二天装夹人前来索要竹夹之时,我对其训戒一番:队屋需要黄鼠狼,明白不?滥杀生灵可耻,明白不?!表面上是为公家也为倡扬德善,实则为祥宝出口恶气。
另一次是和绰号叫“胖墩”的青年一起值守,他年纪和我差不多,但瞌睡大。那个春夜,我正酣睡之际,猛听得“咚”一声闷响,惊醒后发现被子不见了。借着土窗透进的微光往旁边一瞧,竟没见着胖墩,十分诧异,往床下一看,他竟卷着被子睡在地上,鼾声响亮,让人哭笑不得。我赶忙叫他起来,根本就没应答,于是我将床铺拍得山响,他还是没回应。我只好把被子扯上来一点睡在床边,将就着挨到天亮。
他醒来后用手摸着床脚,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觉得不对,还喃喃自语:“咯是何解罗?”让我笑得肚子痛。要是当晚有盗贼来偷东西,怕是把队屋搬空我们还不知道。
年轻,是美好的岁月,荒唐和滑稽也是其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
范精华,湘阴人。毕业于湖南理工学院。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冷水江市作协副主席。发表散文、辞赋、小说、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150余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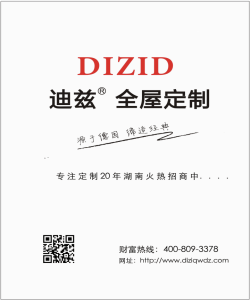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