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精选 ▎卧 书 (文/姜贻伟)
卧 书
文/姜贻伟
我常躺着看书,躺着在一堆书里。天气热,用本杂志扇扇风;枕头低,塞进几本垫垫高;肚子凉,压上一册避避寒……然后,又这本书看几页,那本书翻几张,十几本书刊拿起放下之后,就疲倦了,就合上书一样沉重的眼睛,在书香氤氲中睡着了,于梦里去吞噬那些字的细胞。
这感觉总很美妙,也很残酷。
并不是任何书都能与我同眠。那些矫情的伪书,那些污秽的黑书,那些浅薄的媚书……苍蝇一般让我厌恶!我实在不愿让我的余暇,继续充满世间挥之不去的瘴雨蛮烟。我尤其不愿让我的床上,有一张让我恶心的书页!
我喜欢的书,是那些充满智慧的书,是那些写尽人生的书,是那些开阔视野的书,是那些增长知识的书,是书中那些可嚼可品的文字,是文字中那些飘逸飞扬的神韵……凡是这一类书,我皆愿读之,我皆可卧之。然而,能让我常读之、常卧之,千百遍而不厌、数十年而不弃的书,数来数去仅十余部矣!
那些只能看一遍的书,我就让它们站起来,走进我的书橱里直直地立着。有时没有好的新书看,我就守着那十几本床头书,这本看几页,那本翻几张,不厌不烦,常读常新。但我看这些书,习惯有些特别:第一遍之后,再不从头去看第二遍,而是随便打开书,翻到哪里看哪里。因此,我的这些床头书,就有无数个开头。我也不去记这些书的人物、故事或者术语,我只从它的字里行间,去吸吮语言的营养和沁人的深刻。几乎每一个中午或晚上,我静静地卧着,厮守着它们,在宇宙的深邃里闪现文字的星光,然后像流星的轨迹那样稍纵即逝。仅令这样,我就很满足。我想,书是我睡着前的一杯牛奶哩!
我记得有一次,一位熟人送了我一本书。那是他自费出版的一本集子。对于自费出书,我从不反对。因为古今中外,自费出版的好书也大有“书”在。于是,我把它扔在床上,准备睡觉时再拜读。我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室内温度已降至零。当我脱下裤子,和着上衣钻进冰冷的被窝里,拿起那本集子翻了一下,我就被这本错字连篇、跋序肉麻的集子倒了胃口。我把它放下了,拿起另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没有以往那种惬意的、美妙的感觉了。我感到浑身烦躁不安,好像枕边有一只毛虫在弄我。我当然意识到了是那本集子在捣乱,破坏了我这一夜的全部情绪。可是,我不愿意起来把它扔出卧室——天太冷了!我也不愿意把它扔在床下。因为它还在我的卧室里与我同眠。我辗转反侧,犹豫了很久,终于,我一跳而起,冲出卧室,把它狠狠地丢进了废纸堆!
我也觉得对不起那位熟人,而且,我跟我的挚友谈起这事时,他们也责怪我太苛刻,太清高。我不分辨,也不说明。我想只是我的习惯。我对那位熟人什么成见也没有,我只是——不喜欢那本集子,就像许多人不愿在宴席上吃他不爱吃的菜肴。有什么办法呢?阿门!
我常常在深夜里突然醒来。这时候,我就打开灯,顺便抓起一本书来看。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我的头脑异常清醒。书中的每一个字,像小精灵似的,纷纷地直往我的脑子里钻,那种麻酥酥、甜蜜蜜的感觉,简直是我最大的享受。很多书,我都是这样在半夜里卧着看完的。
有些人常常问我:喂,你的床头书到底是什么书呢?可以借来看看么?我当然不会借。至于那是些什么书,也没必要“坦白”。那只是我喜欢的书,能和我同枕共眠的书,就像你喜欢的书我不一定喜欢,我喜欢的书你也不一定喜欢一样。说不定我一说出来,你也有“吞苍蝇”的感觉呢!
我想,我死的那一天,这些床头书是把它和我一起烧掉呢?还是留给我的孩子?我觉得这问题很难回答。何况,现在我也不愿回答,我还得和它们睡上几十年哩!

姜贻伟,武冈籍,年七十,居郴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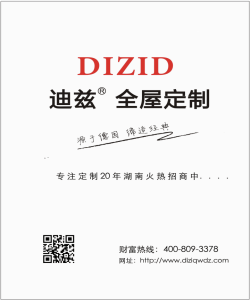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