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着构建民间叙事文学新样态奋力掘进
向着构建民间叙事文学新样态奋力掘进
——晓苏短篇小说集《夜来香宾馆》创作述评
文/刘 赋

【内容摘要】:《夜来香宾馆》是作家晓苏近3年来创作的短篇小说结集。以作家所熟悉的鄂西山村油菜坡为创作背景,通过对油菜坡农人生存境遇与个人苦难的反复吟咏与执着书写,试图以文学的样态,为传统乡村走出困境提供一个全景式的乡村调研报告,从而企图为新时代新农村社会建设提供案例、探寻新路。本文尝试用弗洛伊德心理学批评方法,对作家作品进行研究。
【关键词】:晓苏;短篇小说集;民间叙事文学;作品研究;
《夜来香宾馆》(作家出版社2019年2月出版)是晓苏近3年来创作的短篇小说结集。作为一位勤奋而高产的作家,晓苏创作生命力之旺盛、挖掘转型时期城乡社会矛盾之深刻、书写底层人物内心挣扎纠结之倔强与顽强,常常令评论界叹为观止,让广大读者目不暇接。
结集收录短篇小说14部,以作家所熟悉的鄂西山村油菜坡为创作背景,为我们全景式地生动呈现了一幅转型时期偏于一隅的山乡人民的生存图景,读来饶有兴味,感觉五味杂陈。
晓苏的小说,故事性强,通俗易懂,语言风趣幽默,叙事圈套千变万化,文字令人着迷。纵观他的文学创作历程,不难发现,构建起晓苏先生文学大厦的两座基石,一个是“大学故事”,一个就是“油菜坡系列”。作家的笔下,大量的篇幅,浓墨重彩、淋漓尽致地对原生态的油菜坡世俗乡村生活进行了书写。写出了他们生存的艰难、勾心斗角、贪婪与性的苦闷,以及乡村伦理与道德的失序与失范,看了让人心情沉重。在我看来,收入《夜来香宾馆》的14部作品,潜移默化或者有意无意地受到了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作品中的人物,无一例外,有的顺其自然地展现了“本我”的欲望和冲动,有的在快乐原则与现实制约的冲撞纠结中迷失了“自我”,有的则在社会规范与伦理道德同原始冲动的激烈博弈中实现了自我救赎,完成了“本我—自我”到“超我”的艰难蜕变,成为真正意义上“克己复礼、走向崇高”的“有道德的人”。

▲晓苏教授与导师樊星教授在一起亲切交谈。
收入《夜来香宾馆》结集中的作品,多个篇目都再现了油菜坡山民的原生态的“本我”生存状态。农妇谷珍患上了牛皮癣,乡下郎中谢去病帮她除癣。谢去病欲擒故纵,谷珍从包裹严实到犹豫矜持,从半遮半掩再到心甘情愿投怀送抱,“过了十天,谷珍身上的癣果然除得一干二净了。不过,谷珍把癣除尽之后没有立即回远安,她又在谢去病诊所待了整整一周。”(《除癣记》);山民陶贵,老婆毛英被包工头王羊拐走,二人反目成仇。毛英又被煤矿洞长挖走。王羊人财两空,风雪夜赶回油菜坡,几乎冻饿而死。陶贵对王羊恨之入骨,决意见死不救。听王羊讲叙毛英移情别恋、王羊鸡飞蛋打之事后,忽然生出恻隐,拿出红薯,喂饱王羊,继而同病相怜,同仇敌忾,在风雪夜,就着熊熊燃烧的火炉,二人捐弃前嫌,推杯换盏,推心置腹,相互原谅,并相约结伴同行,“赶在过年之前去平顶山把毛英找回来”(《推杯换盏》);——闭塞,愚昧,冲动,及时行乐,不计后果,放任欲望在油菜坡的沟壑深涧里恣意疯长。你很难看出作家是在欣赏这旷日持久、了无生机、令人不寒而栗的乡村风景,还是以戏谑的心态,叼着一支烟,任心底流血,在冷眼旁观?
我们试着用“自我”理论,来观照《夜来香宾馆》中的几个文本:
油菜坡的三个农民,相约去大城市医院看病,其中一个叫林近山的农民,认识一个当年在油菜坡下乡插队当知青、后来在城里做了小领导的副局长。围绕免费看病与取回无证驾驶的被扣车辆,发生了一连串扯皮拉筋、啼笑皆非的事情。三个人在返程的路上,争论不休。张自榜向林近山讨要陪同的工钱,李兆祥向林近山索要租车费。工于算计的林近山一一拒绝。车上争吵打斗,导致车辆失控,撞上护栏,坠落悬崖,伤势惨重。——三个农民的狡黠、算计、吝啬、贪得无厌,医院院长与行管局长的手眼通天、公权私用、公私不分与对公共资源的挥霍无度、假公济私以及权力滥用,还有基层办事员的阿谀逢迎与对人情社会“潜规则”运用的熟稔有余,无不让我们看到了转型时期城乡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与世俗人情社会的盘根错节和根深蒂固,于嬉笑怒骂中,生动揭示出一幅传统乡村社会在迈向现代化民主法治进程中治理能力低下与公共资源不堪重负的狂欢图景。很显然,这个短篇已经超出了“本我”层面的原生态的单纯追求欲望本能满足的书写范畴,向着“唯利是图的、世俗化的、社会化的”山路在一路恣意狂奔(《看病》);
众口铄金,人言可畏;说好的有,说坏的也有;祸从口出,毁誉参半,负面评价与正面评价,口吐莲花,喋喋不休,莫衷一是。《说的都是一个人》,就是这样一篇象征主义风格浓郁的短篇佳构。清明节前夕,退休老人柴禾回到故乡油菜坡扫墓,他遇到了一个叫做万元的啰嗦鬼。二人结伴同行,到山顶去祭扫。一路上,万元拉着柴禾,一个劲儿地给他数落紧傍山顶墓地的一个叫做龚喜的光棍汉的种种不是。下山返程的路上,当得知龚喜是柴禾的表弟之后,万元忽然在态度上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讲的全是关于龚喜的好话。上山时,万元把龚喜说得一钱不值;下山时,万元又把龚喜说得天花乱坠,其实,说的都是一个人,只不过他的评价判若两人的转折点是在倾听人的角色与被评价人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之后。我觉得作家是在借闲人对龚喜天上地下翻云覆雨不靠谱的道德评价一事,讽刺世俗社会人情中普通民众社会评价的黑白互换与身不由己,对裙带之风盛行的封建文化根深蒂固的无可奈何。故事轻松搞笑,情节怪诞不羁,荒诞的笔墨,表达的却是深刻凝重的社会主题。

▲晓苏教授在联欢晚会上致辞。
《推牛》与《道德模范刘春水》,以冷峻的现实主义笔法,揭示出“假大空”甚嚣尘上、无孔不入的社会时弊,给普通老百姓带来的烦恼乃至灾难,对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屡禁不止的弊端,毫不留情地进行了猛烈批判,揭去了其虚伪的面纱,试图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
在“浮夸风”盛行的年月,“我爷爷”高云天本意上为了保卫自家的耕牛,结果,被公路上疾行的大客车撞飞殒命。镇上将我爷爷树立为舍己救人的典型,由此,给“我”一家带来了无休无止的烦恼乃至灾难。“我”按父亲临终遗嘱,想为爷爷正名,结果却四处碰壁。(《推牛》)
公鸡沟一个叫做刘春水的农民,打了48年的光棍。油菜坡有一个年过六旬的老妪,叫习久芬。习久芬家大口阔,老公、孙子、女儿相继身染重病,女婿弃门而去,生活不堪重负。光棍刘春水自蹈水火,入赘成为上门女婿,帮着习久芬,苦苦操持这个破烂不堪的家。刘春水孝亲敬老、扶危济困的事迹,感动了很多的人。他无可争议地被评为镇上第十届道德模范。镇上要来采访报道刘春水的先进事迹,刘春水却一再避而不见,让人不明所以。刘春水的秘密,无以对外人言讲。
这个故事着实是让人压抑、沉重。习久芬一家的生活境遇,是一个典型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真实案例,是中国落后贫困地区农民困苦生活的一个缩影。习久芬一家四口,丈夫、孙子、女儿三人重病。刘春水一家兄弟三人,都打光棍,48岁了,才成为这个贫病之家的上门女婿。欲望的短暂排遣,让刘春水重新燃起一团生活的热火,顽强挑起生活的重担,帮衬岳母习久芬操持起这个残缺破败的家。生活稍现曙光,孙开蕊便撒手离去。岳母习久芬为了送别与挽留女婿,一面是出于真诚的感激,一面也是长年欲望压抑的本能宣泄,在女儿死后,偷偷摸摸、秘而不宣地成为了女婿的枕边之人。(《道德模范刘春水》)
道德失范,错辈乱伦——这是一个令现代文明人不可思议、本能排斥、感到惊悚、令人扼腕的危险叙事,很显然,它触碰了人类文明与伦理道德的底线,颤动了人们噤若寒蝉、不敢直视的敏感道德与风俗禁忌的神经。站在伦理道德的角度,对此,我们坚决摇头。但设身处地,倘以人道主义的立场加以观照,我们不禁心生无限悲悯。
刘春水的遭遇,实际上是深刻地反映出偏远山区、乃至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较为普遍的因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而导致的大龄青年婚恋难的问题,揭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与女少男多的人口结构性矛盾。这样,作家晓苏先生就以史学家的责任与勇气,敢于正视和直面这一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以习久芬个人命运的辗转沉浮与一家人的遭遇及隐忍苟活,来观照生活在当代中国偏远乡村最底层人民的生存境遇,对他们的左冲右突、顽强抗争与执着坚韧而给予深切的悲悯与同情,为他们虽身处逆境仍倔强生长的小草精神而秉笔直书,写出他们的无奈,写出他们的抗争。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当庙堂文化还在为“生存还是毁灭”而拔剑四顾的时候,以习久芬、刘春水、春桑、侯己、张开凤、高云天的儿子为代表的这一个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草根,为了原始欲望的排遣,为了挽救残破的家,为了基本的生存权利,还在贫困线、温饱线与欲望线上苦苦挣扎,在他们这里,也有着对夫妻敦睦的呵护,对人性光辉的凝视,对食能裹腹的希冀,对兄友弟恭的守候,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好死不如赖活着”,写活了底层人物命运的沉浮挣扎,找准了人性幽暗彷徨的山川径流,揭示出了以油菜坡为发散点的城乡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与一言难尽,在着力构建民间叙事文学新样态、试图开挖出一条能够连通民间文化长河、打通主流与支流、贯通庙堂叙事与草根书写、冀希望臻达“既要有意义,又要有意思”、“既要可读,又要耐读”的创作风格方面,我们能够窥探到晓苏30余年来,顶着巨大压力执着书写的宏图志向!
短篇小说《撒谎记》与作者早年书写的引起文坛广泛关注的《侯己的汇款单》有异曲同工之妙。“我”的儿子赵弯酒后开摩托车,翻下了山坳,摔断了腿。在医院院长善意的教唆下,为了给儿子争得一张公费合作医疗的假证明,“我”和妻子被动周旋于医院院长、村支书之间,送烟买酒请村支书吃野鸡火锅,忍气吞声,甘受无赖邻居的漫天要价与无耻讹诈,历尽重重波折盘剥,最终如愿为儿子开好了公费合作医疗的假《证明》。但令人哑然失笑的是:“医院结账时,按规定报销了三千多块钱”,妻子艾蒿估算了一下,“我们把送礼、请客和那头肉猪加起来,也差不多有三千块”。艾蒿欣喜地说,“总的算起来,我们也没吃亏,多少还占了一点公家的便宜”,看来,“这次撒谎总算没有白撒”。(《撒谎记》)作品表现出了世俗乡村人情社会根深蒂固的“潜规则”与“关系网”对底层人物的因袭与束缚粘连,温水煮青蛙,置身其中,不得其解,人人既是推波助澜者,也是深受其害人,从而深刻揭示了传统宗法制乡村社会结构治理之艰难与新农村建设的任重道远举步维艰,大声疾呼清新清爽清朗诚信友爱文明法治的新时代乡风早日劲拂,涤荡陋俗陈规所卷起的瘴气乌烟。
《两次来客》,让我想起了作家从前写过的作品《粉丝》。这个短篇,更像是一个心理小说。金鼎好容易在油菜坡建起了一栋三层的新式楼房。新屋建好以后,他先后接待了两位客人,一位是从襄阳来的表弟赵宽,一位是来自宜昌的表哥李帽。金鼎先是精心张罗,置办新衣新茶新餐具,好酒好肉好招待。但表弟赵宽一阔脸就变,不谙人情世故,开着豪车,炫富露富,行事张扬,唯我独尊,对金鼎的热情接待毫不领会,横挑眉毛竖挑眼,全然不理会金鼎的深情厚谊,显摆一番之后,匆匆离去,让金鼎心灰意冷;表弟前脚刚走,表哥接踵而至。心不在焉、受了刺激的金鼎,对表哥李帽的接待不冷不热。但生活困顿的李帽,对金鼎所取得的建设成就赞不绝口,对金鼎的幸福生活由衷羡慕,对金鼎粗茶淡酒的热情接待满怀感激,让金鼎感觉很有面子,心里很热乎,表哥李帽走的时候,金鼎还“非常爽快地借给了他500块钱”(《两次来客》)。这个故事试图提醒人们要恪守主客之道,切莫喧宾夺主,主次不分,以免善意的初衷,被不合时宜的表达,搅黄了亲情与友情。同时,也对金鼎之流的普通人爱慕虚荣、好面子、摆排场、讲阔气的小农意识进行了善意的揶揄。“适可而止,过犹不及,把握分寸,学会赞美,体己及人,调控情绪,不以誉喜,不以损忧,笑对生活”,作家是在以这么一个世俗庸常的幽默故事,提示我们在物欲横流、欲念滋长的喧闹世界里,守护内心的宁静该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是普通人情社会的生活哲学,有的人深谙此道,通达圆融,有的人却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到头来四处碰壁,损人不利己。
油菜坡建筑老板周同仁财大气粗,乐善好施。他生病后,他的三个相好女友的丈夫松、竹、梅结伴到医院来当陪护。四个男人,同处病室,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遮丑,不避短,不矫情,直面问题,正视现实,尴尬轻松化解,各自相安无事。“几个护士进来查房,看见四个男人有吃有喝,还有欢声笑语,不禁感叹不已”。护士长笑眯眯地对周同仁说,“你真会来事,硬是把病房搞成了俱乐部”。(《同仁》)
这是一部“勿以暴力抗恶”、铺陈人道主义曙色的山乡轻喜剧。很显然,像这样共处一室、其乐融融的场景,不太符合普通人们的生活常识。我注意到,在晓苏的笔下,《嫂子调》、《光棍们的太阳》、《花被窝》、《回忆一双绣花鞋》、《我们的隐私》、《有个女人叫钱眼儿》、《酒疯子》、《养驴的女人》、《除癣记》、《陪读》、《送一个光棍上天堂》、《人住牛栏》、《帽儿为什么这样绿》、《陪周立根寻妻》、《花嫂抗旱》、《传染记》、《父亲的相好》等多个篇幅,都对油菜坡人的两性关系有过较为集中的书写与表达。在作家的笔下,油菜坡的男人女人,热情率性,大胆炽烈,对两性之间的交往与表达,怀抱着较为开放、包容的态度。评论家樊星曾对地域文化之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有过深入的研究。我也曾经对晓苏作品笔下的这类风俗,从地域文化上进行过探讨。油菜坡地处鄂西,深受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影响与熏陶,恶劣艰苦的生存条件与秀水青山的自然风光,浸润和塑造了油菜坡人既保守又开放、既现实又浪漫、既冷漠又热烈、既剽悍又柔软的地域文化,恶劣的生存条件,磨砺了油菜坡人民坚毅执着、以苦为乐、百折不挠的山民品格。生活本已艰难,何妨纵酒放歌?鄂西一带,一年一度、至今仍生生不息、载歌载舞的“女儿会”与“桃花节”,为婚前婚后的男女交往,搭建了表达浓情爱意的节日的狂欢舞台。我想,正是有了这样的对男女之爱的默许与包容的爱的土壤与特色独具、多姿多彩的温润民风,或许才有作家笔下这些令人开怀一笑甚或是相见甚欢热烈场景的铺陈吧?——生活一如《甘草》,苦中作乐,苦尽甘来,妥协,又何尝不是身处逆境中的底层人物的一种生存智慧呢?逆来顺受,以柔克刚,大智若愚。
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人格结构的最高层次,属于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是道德化的自我,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内化而来,其形成是社会化的结果。超我遵循道德原则,它有三个作用:一是抑制本我的冲动,二是对自我进行监控,三是追求完美的境界。
小说集中余下的四个短篇,其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在超我原则支配下,抵制欲望,恪守礼制,向着道德的高坡努力攀援的人,他们是穷乡僻壤间滚石上山的西绪弗斯,是油菜坡人的希望,寄托着作家的社会理想。
已婚山村音乐教师李采是父亲的相好。年轻时主动追求父亲,两情相悦。偷偷摸摸的爱情,在社会秩序面前不堪一击,很快劳燕分飞,无疾而终“见光死”;父亲婚后,生下女儿“我”,李采视同己出;为治好“我”母亲的羊角疯病,主动上演“苦肉计”,直面“我”的母亲,任其撕打宣泄;“我”的儿子考上了十堰的大学,年老的李采忙前跑后,置办安顿开学行李衣物,殷勤照看。“不思量,自难忘”,异于常人分手情侣的老死不相往来,父亲的相好李采几十年如一日,岁月虽逝,意笃情坚,把爱放在箱底,将爱情化作友情与亲情,浓情如酒,细水长流,悠远绵长,润物无声。而这一切,都是在恪守社会道德与伦理规制的框架下,循规蹈矩地默默运行,读来让人心生温暖与感动(《父亲的相好》)。
妇女主任张开凤,怀着一颗有可能即将成为未来新村支书接班人的强烈事业心,忙前跑后,昼夜操劳,夙夜在公,在极度压抑个人婚姻生活不幸的同时,担任婚姻“救火队长”,辗转村庄墩台,苦口婆心,现身说法,周旋于多个因夫妻感情不和而意欲离婚的吵闹家庭之间,疲于应对,努力说服与她有着类似遭遇的同村妇女,试图挽救一个个濒临离婚散伙的家庭,弄得是心力交瘁,但最终的结果,镇上宣布的村支书却另有其人。忍无可忍的张开凤,不再纠结于社会职务,听从内心的召唤,立即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救火队长”,到头来,成了全村第一个敢于“放起身炮”的大胆争取妇女个人独立自由的先锋,反讽意味明显。(《妇女主任张开凤》)
农妇胡葱在她四十八岁生日的那天,在镇上邂逅了年轻时的旧相好丰收。丰收是大学生。胡葱满怀期待,希望能在一家叫做“夜来香”的旧时的宾馆旧情重温,与风度翩翩、已在襄阳一所中学当上了副校长的旧爱重温美好。但时过境迁,丰收早已忘却了从前,在生日之夜,将独守空房、苦苦等待缱绻缠绵的农妇胡葱忘得一干二净。半夜时分,正在水泥工地抬水泥板的丈夫明礼,从工地寻到宾馆,掏出两盒“百雀羚”牌子的雪花膏,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胡葱。“满目青山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胡葱心头一热,夫妻们平生第一次在距家咫尺之遥的夜来香宾馆共度良宵。(《夜来香宾馆》)
这部短篇,很有意思,把它同《父亲的相好》拿来做比较,发现二者都是在表达女性渴望温暖与爱怜的主题。一个是时移情坚,初心不改,爱河涌流;一个则是光阴易逝,年华催老,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惆怅满腹,失去了就不再重来。我们不能强人所难,要求所有的旧爱一定能够开出繁花,结出蜜果;我们也不能指望失去的美好,一定能够沉爱泛起,昨日重现。时光机有时候可以穿梭、倒流、回溯、重温,但更多的,则是年华流水,记忆尘封,无迹可寻,带给人的,只有怅惘与失落。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记忆虽然美好,摆在面前的,仍然是那只旧木盆。作家试图通过这个故事,告诫劝慰每一个自作多情、想入非非、寻梦而不得的曾经年轻的我们: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拥抱生活,活在当下,真实的生活,该是多么美好!
和作家早期作品《甘草》、《麦芽糖》立意异曲同工,《吃苦桃子的人》,是这个小说集的压轴与扛鼎之作。
大龄光棍憨宝,老实巴交,形容丑陋,但他有着一颗金子般闪光的心灵。他放牛,照顾无父少娘的侄儿,孝顺80岁的老娘,成天喜食还未成熟的苦桃子,见美味而不用,弃华服而不着,怀美色效下惠,握箪食心自甘,临诱惑而木然,固守清贫,甘之若饴,不为所动。
作家精心设计了憨宝这么一个固守清贫、安之若素、拒绝金钱、美色、美味、好衣、好工作、舒适环境的诱惑、苦守贫瘠乡村、以苦为乐、爱吃苦桃子的人物形象,试图以此对抗城市文明的繁华喧嚣,固执守望淳朴乡村。憨宝的形象,倔强,质朴,孤独,以苦为乐,热心快肠,济人危困,外表虽然邋遢,内心却一尘不染,美德善行如镜子般闪闪发光,映照出置身于日益迫近、让人心慌气短的城市化进程中快速驶过的重型碾压机之下的人们的焦虑、慌乱与惶恐,让人很容易想起《巴黎圣母院》中那个叫做卡西莫多的古教堂敲钟人,象征意味明显。

▲本文作者 刘赋。
《龙洞记》、《怀念几件衣服》、《走回老家去》、《油渣飘香》、《麦芽糖》、《甘草》、《海碗》、《姑嫂树》、《姓孔的老头》、《留在家里的男人》、《村里哪口井最深》、《我的三个堂兄》、《让死者瞑目》、《侄儿请客》……,与作家早期这些作品一脉相承,作家一方面在不遗余力地赞美油菜坡世俗乡村社会自然风光的旖旎与淳朴民风的韧劲恒久,痴心守望与尽情抒发对日渐式微的传统农耕文明的美好记忆与无边乡愁,同时,也流露出对城市化浪潮裹挟之下现实乡村的凋敝与失序失范的苦闷和彷徨。通过对鄂西山村油菜坡农人生存境遇与个人苦难的反复吟咏与执着书写,作家试图以文学的样态,为传统乡村走出困境提供一个立体的、全景式的乡村调研报告,从而企图为新时代新农村社会建设提供一个个立体的、全景式的生动案例。这一点,是“油菜坡系列”创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也是作家在努力构筑新的民间叙事文学堤坝的一张总蓝图。
2019年7月19日星期五1稿于昆明
2020年9月10日星期四定稿于北京 7800字
【简介】
作 家:晓苏,著名作家、编辑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发表小说600余万字,屡获文学大奖。
本文作者:刘赋,湖北监利人。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后,教授级高级政工师。先后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担任记者、地方党政部门挂职锻炼,现供职于中央企业。出版有长篇小说《戏台人生》、《新四军战士刘金汉传奇》、中短篇小说集《父亲的土地》,理论专著《中国共产党舆论监督工作研究》、《学习与思考——刘赋同志理论文章自选集》等5部。在《红岩》、《芳草·潮》、《文学教育》、《语文教学与研究》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逾百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湖北日报》、《调查与研究》、《江汉论坛》、《湖北社会科学》、《理论月刊》、《中国改革》、《电视研究》等报刊发表调研报告、文艺评论、理论文章60余篇,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略通音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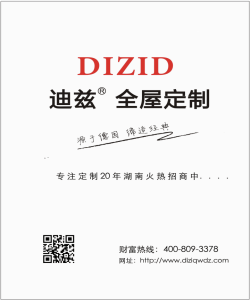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