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夫子 ▎文/肖鲁仁
本站网址:www.ddsjmt.com
斋夫子
文/肖鲁仁
斋夫是一个传统名称,是指旧时学舍的仆役,类似今天学校的勤杂工人,具体包括炊事、卫生、安保等一类的人员。在计划经济年代,斋夫虽属全民所有制岗位系列,但不属事业编制,而是属工人编制。在上千人的学校,有二至三个这样的工作岗位;在三、五百人的学校,通常只配一个这种编制的工人。许毅春就是在只有一个工人编制的学校当斋夫。

我父亲是那所学校的校长。本来,斋夫与伙夫、贩夫等名称一样,后面是不加一个“子”字的。这个“子”是我父亲加上去的。据当年与我父亲共事的老师说,不知道为什么,肖校长无论是批评人还是表扬人,总要自觉不自觉地说一句有“斋夫子”字眼的话。
由此可知,许毅春作为斋夫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一
许毅春的父亲许伯恒比我父亲大十多岁。解放前,他们在同一个私塾先生那里启蒙。我父亲后来回忆说,一本《千字文》、一本《三字经》、一本《增广贤文》、一本《幼学琼林》,其他同学读几遍,最多半年就能背诵,可是许伯恒读了三年,仍然结结巴巴记了上句,忘了下句。问他“易涨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是什么意思,他说:“下大雨,河里涨水啦。咱们那条河不宽,涨、涨三尺高……应该很容易……”不等他说完,先生便动怒了。不知用戒尺打了他多少手板,但他就是记不清书本上的东西。没法子,先生后来罚他劈柴煮饭,不料许伯恒做这些事简直无师自通,尤其是煮饭,软硬、火候把握得极好。放学后,他还主动到小河里摸些鱼虾帮先生改善伙食。因此他尽管不会读书,先生也很喜欢他。
我父亲在那一班学生中成绩名列前茅,后来他跳级去了另一个学校。许伯恒一直在那位先生那里念书,念了几年实在升不了学,就干脆回家结婚生子去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父亲成为了家乡一所学校的校长,而许伯恒在家生养了七个子女,大儿子许毅春已快二十岁了。一天,许伯恒请年逾古稀的老先生一块到学校为许毅春“找差事”。老先生说:“延先生(我父亲名字中有一个延字),伯恒家老少十口人,负担重哩。他大儿子忠厚勤快,当斋夫是一把好手。你若收了他,那一家子就好过多了。”父亲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二
作为学校勤杂人员的“斋夫”,许毅春果然是一把好手。他上岗不到一年,就证明了这一点。大家总结了他的三大绝活:一是下厨,他做的饭菜很对大家的口味。学校的饭不是用铁锅煮,而是用大蒸笼蒸,原来的饭不是干就是稀,有时还没熟,许毅春蒸的饭不仅软硬适度,而且量也好像要足些。二是打铃,他不看钟也拿捏得准时间。学校只有一面经常“罢闹”的闹钟,放在校办公室;还有一块上海牌手表,戴在校长的手上。有时,这两样他都不能依靠,只能自己“踩着点子”打铃。我父亲对过手表,他告诉大家:“许毅春不看钟表打铃,误差能控制在两分钟以内。”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至今谁也不知道。三是开门,这里的开门不是早晚开门关门。学校大门是那种老旧的木板门,里外看不到人,但凭脚步声,许毅春就知道是谁来了,该不该开门。学校好几十个老师,他能分辨出每一个老师的步幅、轻重以及敲门声,尤其是校长来了,更远的距离他也能听得出来。别人问:“你怎么知道是校长来了?”
许毅春说:“校长的步子重些。”
“教体育的刘老师步子也重呀。”
“两人钥匙圈的声音不同。校长那一圈钥匙经常用,里边还有两把铜钥匙,声音比较脆;小刘老师虽也有一串钥匙,但里边有用的只有一把,其他都是作陪衬的铝铁钥匙,声音当然不一样了。”
大家听了,觉得许毅春没有去搞公安,简直是浪费人才了。
三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农村边远地区,匪患并未绝迹。一年冬天的深夜,一股土匪举着长矛大刀吵吵嚷嚷从外乡扑过来了,学校的秀才老师们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尽管校长在学校礼堂号召大家鼓足勇气,齐心拒匪。绝大部分人都不敢拿起菜刀扁担与土匪对峙,一个个退到小房间里,拴上门,躲在被子里发颤。只有许毅春拿两根横木顶着校门,大喊着,用一把邻村民兵连放在学校的梭镖敲着脸盆与土匪对峙。后来,土匪用大刀在校门上砍了一个洞,正要伸腿进去,许毅春眼疾手快,一梭镖上去,正扎在土匪的大腿上。这是一个土匪头目,见他负伤,其他土匪慌忙把他拉回去,嗷嗷叫着逃跑了。
三天后,县宣传部、教育局派人送来了“勇战恶匪,护我桑梓”的锦旗。据说,在这拨土匪抢劫的几个学校中,唯有父亲所在学校未受大的损失,而且附近村民也躲过了灾难。其他学校损失都在千元以上,相邻学校的一位女教师还受到了土匪的调戏和猥亵。父亲要县里的人专门采访工友许毅春。许毅春对上级领导说:“全凭校长指挥得当,广大老师齐心协力,我们才战胜了土匪,保护了学校的财产没受损失。”后来,县里拨了几百元奖励学校员工护校有功。许毅春坚持要和当时在校的老师平分,他不多拿一分钱。父亲作为校长只好请他喝了一次酒,其他几位校领导作陪。席间,大家对许毅春说:“护校你立了头功,多拿一份奖金是应该的。”
许毅春说:“我多拿了会睡不着。”
“这从何说起?”
“我怕他们杀回马枪。”
“土匪窝都端啦,你怕什么?”
“世上的坏人消灭得了吗?我不图出名,平平安安睡得着就好。”
父亲摇着他的肩膀说:“斋夫子,你硬是一个斋夫子啊!”
四
三年饥荒,饿不倒伙房。在粮食全面短缺的日子,到处是双腿浮肿,走路摇晃的人,偏偏许毅春在这苦难的日子里看到了缕缕春光向他射来。他每天心情最激动的时刻,是开饭打菜的那几十分钟。平时那么高冷的年轻女教师,那么热切地望着他,眼睛里有兴奋、有期待、有怜爱、有温柔,总之内容丰富,人间一切美好的情感都蕴含在其中。有时,她们还、还什么呢?许毅春想起了最近在话本小说上看到的一个词“蛾眉宛转,香唇微启”:“小许师傅,你怎么越来越白嫩,越来越帅呀!”声音极熨帖、极温暖,烘得他心潮澎湃,全身颤抖,连拿勺的手也把持不住。
一次感冒无情地击碎了他这种美好的想象。本来,一年到头许毅春难得一次感冒打针,但他想起了每次见他都娇滴滴地说“你好帅”的生理老师兼校医吴曼妮,这不刚好是见面说话的好机会吗。他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校医务室,可是吴老师或者说小吴医生却格外严肃。他说个不停,小吴医生的回答除了“嗯”就是“哦”,没有一句多余的话。最使他尴尬的是打针时,小吴医生拿注射器的手不停地颤抖,许毅春说了句“你拿注射器的手可以不颤抖吗?”。小吴医生说了那天唯一一句完整的话:“那你打菜时拿勺的手为什么要颤抖呢?”
小吴医生的那句话把许毅春打回了原形。他终于明白,学校美女教师虽多,但他是够不着的。就像《西游记》里“三藏不忘本,四圣试禅心”那一回,八戒身边蹁跹起舞的美女再多,他也是不可能撞到“天婚”的。
走出学校这个小天地,许毅春发现他的“优势”还是很明显:他是吃商品粮的,比起吃农村粮的不知要好多少倍。他的全民所有制编制又要好过小集体大集体,比如种子站、农机站、水电站、修理厂、供销社等。他在学校属后勤、服务系列,虽是敲边鼓的那一种,但总共4个勤杂人员,只有他一个是“正式的”,最关键的是他拿菜勺把,在那个年头,这就是一种无形的地位。那几年他相亲像走马灯似的,相了一个又一个,一个更比一个“淡”。到后来人相“疲”了,仍没遇到一个满意的。这时的许毅春年纪眼看着往三十岁上窜,在那种边远地区,这个年龄还没成家,多少会引起周边的一些闲言碎语。这可急坏了家里父母。他们专程到学校,拜托校长关心。
不到半年,校长为许毅春牵了一回线。开头许毅春没太当回事,毕竟牵过的“线”数也数不清,加起来恐怕有一大把了。校长看出他的心事,要他莫气馁,打起精神来。相亲那天早上,校长还送了一套夫人做的蓝卡其布中山装给他,要他换上,“去去烟火味”。谁知,这次和姑娘一见面,许毅春就愣住了:对方细皮嫩肉,眉眼水灵灵的,要身高有身高,要腰肢有腰肢。这哪里是吃农村粮长大的呀,简直大大胜过了学校里的美女老师。而且家庭背景还“出彩”:父亲是大队支书,哥哥在部队当连长,弟弟进了县税务局开汽车。许毅春不知不觉脸红了,手不知往哪里放,支书娘子喊了两次“请坐”,他也没听见。后来,姑娘在他耳边说:“我娘要你坐下,你怎么不坐呀。”这时,许毅春才缓过神来,结结巴巴说:“啊,好。不,不要客气。我衣服是、是校长送的,我怕坐皱了,下次出门穿……不好看了。”他的话引得支书一家忍不住笑了。说:“见过实诚的,但没有见过这样实诚的。”
许毅春的婚事就这样成了。
五
时光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这是鲁迅文章中的语言,它指的是几个学生的生命不可能对北洋政府以及杨荫榆所领导的学校当局形成根本性的冲击。不过,上个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确进入了一个不太平的年代。
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斗私批修,狠斗灵魂一闪念”等口号的鼓动下,相互揭发、匿名告状、诬陷打击等流氓哲学、地痞手段盛行,学校先是成立“革委会”,叫做“教育要革命”,然后是狠批白专路线,叫“停课闹革命”。这时我父亲已“靠边站”了,代替他的是告黑状起家的文革斗士。但父亲头脑是清醒的,他时常告诫许毅春等他认为“信得过”的人:“不要出头,不要掺和。现在是个乱世,但终究是要过去的。”
其实,许毅春正站在风尖浪口上,因为斗士们正在拉拢他。他出身好,是典型的工人阶级,有一定文化水平。斗士派头头、新革委会主任还表扬他“能团结大多数革命群众。”不久,工宣队进驻学校,为了争夺领导权,双方展开了白热化的斗争。工宣队队长是县副食品公司经理,手里有“尚方宝剑”,另外还掌握一定的紧缺生活物资,部分老师已被他“拉拢过去”了。斗士派本就靠斗争起家,熟门熟路,重要岗位都有他们的人把守。一天,斗士派头头找到许毅春,要他“提高阶级警惕性”:工宣队长正在拉拢吴曼妮,给了她好几张购物券,很危险。“据可靠情报,这只笨熊还想和吴曼妮乱搞男女关系呢。只要你报告有价值的线索,可以吸收你进入学校革委会。”许毅春压根就看不起那个革委会,给什么券和他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他看不惯“乱搞男女关系”那一条,尤其是打吴曼妮的主意,这口气他怎么也咽不下。一个月以后的凌晨两点钟,斗士派头头接到许毅春所提供的信息:工宣队长到吴曼妮房间去了。是夜,火光大作,喊声雷动。工宣队长与吴曼妮就这样生生的从房间里被揪出来,衣服都没有穿整齐。
这件事的处理结果异常严厉:因为破坏军婚,工宣队长被开除党籍干籍,判刑3年。吴曼妮降职降薪,被调离原单位。看到吴曼妮落魄离校,许毅春肠子都悔青了,他站在学校后山坡上,大声吼叫:“我没想要怎么样,才进去十分钟,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啊!”许毅春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确实是“没怎么样”,但工宣队长与吴曼妮在县城早已经“怎么样”了。只是斗士派拿不到证据,不好下手罢了。他们知道,只有许毅春有这个能力,能让他们抓到现场。一抓到现场,其他事情就好办了。直到这时,许毅春才发现被人利用了。
父亲对许毅春视若己出,从没有对他严厉过,这次把他喊到家里,不由分说,先重重抽了他两个耳光,然后恨恨地说:“你个斋夫子,猪一样的斋夫子。”许毅春泪如雨下,跪在地上说:“我错了,你狠狠抽吧,抽死我算了。”从父亲房间出来后,许毅春直奔斗士派头头、学校革委会主任家里,见到他后,也是一句话不说,两个重重的耳光直接摔在他脸上,然后咬牙切齿说:“你要杀人,我也没办法,你拿我当刀使干什么!”革委会主任被他打懵了,捂着血红的脸说:“你疯啦,你疯啦,平白无故打人。”但他毕竟心虚,不敢起高腔喊人。这个事吵开了,他也无法交差。
六
没过多久,我父亲被派到专署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学校离专署五七干校150公里,有一半路程只能步行。许毅春坚决要求送父亲,他挑着行李和父亲一起在大山间行走。父亲说:“我走后,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家里的事请你多照顾一下。”
“这个自然,我每星期会去看看。”
“我家毛坨(我的乳名)初中快毕业了,如果他不读高中,我想让他招工当斋夫,到时你带带他。”
“毛坨聪明,还是让他读书吧。”
“读书有什么用,我今天落到这个地步,还不是多读了几句书吗?况且,现在的学校也教不了书了,还不如到你那里学徒,图个安稳。”
“您放心,有我一口饭,绝不让他喝半口粥;有我一口肉,绝不让他啃半根骨头。七蒸八炖十二炒,保证他一年掌勺,两年出师。”
“行啊行啊,你这个斋夫子,知道你有两把刷子,我相信你。”
山路崎岖,蜿蜒曲折。前面就是湘中雪峰山主脉,山路延绵五十余公里,要过山才有客栈。许毅春看天色不早,建议就此歇脚。父亲说:“天气预报明天有暴风雪,最好趁天晴赶路。”又说:“下一站火铺太远,走夜路的话,就怕山上野兽伤人。”许毅春说:“这个好办。”他麻利地从行李袋中翻出一把梭镖头,就在路边树林中割下一根杉树枝,削皮,套头,墩紧,一气呵成,然后递给我父亲说:“既当拐杖,又可防身。”父亲接过,往地上一点,长长松了一口气:“有了它,咱就不怕啦。”他下意识哼起了以前开会作报告时常引用的几句毛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许毅春听着这诗篇,凝望着远处偏西的红日下延绵起伏的山峦,霎时心头涌起一股按捺不住的豪情。他挑着担,一手揽着纲绳,一手携着父亲,自信满满上了雪峰山。
作者简介

肖鲁仁,1964年生,湖南娄底人,工商管理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在新闻媒体历任记者编辑以及总编室主任等职务,在新闻第一线工作10余年,具备较丰富的采写编评经验,个人作品曾十余次获得省级以上奖励,获奖作品涵盖新闻以及散文、小说等体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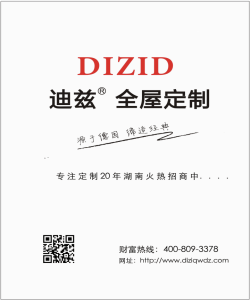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