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谈论新冠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当我们在谈论新冠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文/贺奕江
我在武汉的朋友说,他是在封城之前离开那里的。当时他只是随口一提。我们会本能地保护自己远离可能存在危险的地域。那差不多是这场疾病开始蔓延的地方。我不由自主地会想起,他有没有想念过家乡。他是个沉默寡言的男孩,即使是在之后更艰难日子里也经常是如此。他还喜欢喝咖啡,讲摸不着头脑的笑话,跟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有着奇怪的癖好。
欧洲人第一次到达美洲时,探险家们身上携带的对他们来说无害的病菌,对当地人来说确实无法言说的灾难。在那一百年里有数万没有免疫这种跨海而来的疾病的能力的土著人因此而死去。那些病菌的染色体里似乎还隐隐包含着着那些信仰仁慈上帝的人们对异端的仇恨;在同一时期,鼠疫夺去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性命如此平等,自然从未偏颇它的观点。
即使是在现代医疗普及的今天,最能威胁人的也是那些看不见的事物,仇恨,秘密,同情,愤怒,以及微生物。
大家坐在家中常做的事是什么呢?远程交流早已搭建好,病毒并不会通过光纤和卫星信号传播,但人们的情绪会。恐惧和疑惑在圈子里如同核爆炸辐射一般扩散,效果并不亚于实物。高传染性疾病考验冲击着从古至今人们建立的这套文明系统,它们到底运转得如何?结构松不松散,意志能否坚定?此时我们还看不到结果。
读书吧,获取知识貌似是消遣时间的好渠道。同时人们会在历史里汲取教训,了解过去的祖先们对付瘟疫的方法。我们是否有获取知识的更佳媒介?我们是否会对电容屏幕上所展示的内容漫不经心?总会有一些空间要让给会误导的讯息的,更不要说那些别有用心的作家们。在总喜欢怀疑的人群当中,似乎只有历史可以相信了。那些报道的数目和传播的速度总是会被夸大和低估——真实信息的传达是否符合规定,是否能保持群众情绪稳定,是否影响股票走向,延期选举,汇率变化?
看看宁静的夜晚。那些在天空中轰鸣的道路,如今相当地安静。偶有维护自由之名的人们走过。地球的暗面寂静了不少。那天晚上,我那同样在受着禁足之苦的朋友突然告诉我,你能在靠近旁遮普的小镇里看得见喜马拉雅山的面貌了,能在水城威尼斯看得清楚河底了,动物们在柏油路上四处张望,自然似乎在默默窃喜。我们在水凝铸成的房屋内踱步徘徊,同时等待着消息和自由,悼念逝者。
我喜欢骑单车,我也喜欢空旷的无人之处。可是很快孤单便代替人群包围了我。虽然没有站在那些尸体中间无声地哭泣过,但想到每一个人都曾经有机会与我有一面之缘,却又被夺去了珍贵的性命,伤感便会很快袭来。悲剧就是这样从生活中诞生的…剥夺所爱之人,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梦境里永远有他们的影子。
沉入睡梦中吧,等待着又一个禁闭的明天。可能你的朋友还在不远的大洋对岸,或者在寒冷的山脉以北。我们之中从来不缺乏有奉献精神的勇士。难以割舍的情感,通过文字,图案和声音表达出来,我们无需担心那种情感会伤害到任何事物,那是最纯真的对生命的敬畏,任何批评家都不会去针锋相对。
“给人类创造一个强大的敌人,之后他们就会停止内战,团结一心了。”智慧的生物们似乎过于自满,他们从灰烬和海洋当中诞生,却对其本身的优秀品质了解甚少。不过至少我们在学习。我们永远期待着活下去,从被子里站起来的时候,还能看见明天的光明,这是动物的本能;我们希望自己关心的人也能活下去,因为你了解并爱着对方;希望所有人都能度过这场灾难,这是因为宇宙里自我的孤独。会有人选择不言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多愁善感。
这里的每一句话你或许都听说过,甚至你,未曾谋面的本人言说过,你可能会把它归类为一种观点,一个想法,甚至一个笑话…不过不用担心,你总是可以仔细阅读我所信仰的立足在人们当中流传的故事。它们漂浮在带有香气的油墨之上,性质稳定,带来遥远的遐想,并且短时间内不会消失。

作者简介
贺奕江,男,长沙人。籍贯湖南醩陵市,1999年12月16日出生于南京市。2017年文艺出版社发表其处女作《我所没有告诉您的故事》,2019年《楚风》杂志发表其诗歌《无题》。现就读于长沙某大学二年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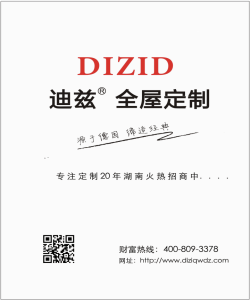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