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邦散文赏析 ▎擦皮鞋的女人
擦皮鞋的女人
文/刘克邦

每天上班,我都要走过那段不算短也不算长的整洁漂亮的人行道,每次都被那赏心悦目美不胜收的都市美景所陶醉与痴迷。
这条路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将原贯穿市中心的京广线改建而成,可能是唐代诗人谭用之“秋风万里芙蓉国”和现代伟人毛泽东“芙蓉国里尽朝晖”等脍炙人口的诗词佳句激发了城市管理者的灵感,这条路被命名为“芙蓉路”。
“芙蓉路”,虽不见芙蓉花开,但绿色葱茏,花团锦簇,香樟、女贞、桎木、杜鹃、月季……一畦畦,一行行,婀娜多姿,争奇斗艳,为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市更添了几分美丽和灵动。
年年依旧,月月如此。我每天上下班穿行在这花街美景之中,神清气爽,喜不自禁,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和烦恼一扫而尽。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在这条亮丽整洁、人来人往的人行道上来了一个女人,一个不同寻常带着孩子擦皮鞋的女人。
她,三十开外的年纪,身材矮小瘦弱,好像是带病之身,身上罩着一套半新不旧布满灰尘的衣服,比巴掌稍大一点的脸庞蒼白中带着肌黄,皮肤粗糙而略显浮肿,两个颧骨高高突出,一双眼睛暗淡无光,像湿土地里的牛脚印,深深地陷了下去,携一把只有在乡村土屋才能见到的竹编小靠椅,提一只装满踏脚木墩、擦鞋布、鞋刷子、鞋油、鞋腊、瓶装水等擦鞋工具的竹篮子坐在路边,见有行人走过,不停地吆喝:“擦鞋啵!擦鞋啵……”
在她身后,站着一个小男孩,看起来不足五岁的样子,同样的营养不良,瘦骨嶙峋,头发浅黄而蓬乱,两手黑不溜秋,衣服油光闪亮,好像从未没洗过脸洗过澡换过衣服似的,从哪里都可以抠得下一块一块的污垢下来,唯有两只小眼睛晶莹透彻、炯炯有光,不时地好奇地顾盼着眼前热闹非凡的都市街景和人车洪流。若见得一群衣着时髦的帅哥靓妹们拿着香喷喷的烤鸡腿烤香肠,边吃边走边说边笑从他身旁经过,一双眼睛便睁得老大,一眨都不眨地瞅着,盯着,跟随着,直到他们渐渐远去……
人心都是肉长的,谁家没有过幼儿?谁又不是由弱小无知的孩童长大?见到孩子那嚅动的嘴唇,饥饿的眼光,可怜的神态,孱弱而病态的形体,我的心在隐隐地作痛……
后来,我在需要擦鞋时,都尽可能地找她来擦。她擦鞋特认真,擦鞋用的鞋油比别人多,花的时间也比别人长,每次擦鞋总是小心翼翼,慎之又慎,生怕弄脏了你的裤腿和袜子。鞋子擦完了,还要前前后后反复查看一遍,生怕留下了一点泥土一点污迹,或者是擦得不光亮。
每次擦鞋,我都有意与她攀谈几句,渐渐地,从她口里了解了她的经历和不幸:她住在洞庭湖边,丈夫早年去广东东莞打工,一次意外事故,抛下了她和不到一岁的儿子,以及年过花甲的老父亲走了。从她过门起,公公就患肺结核长期卧床不起,丈夫在生时,就曾租过车子到县城到长沙就诊,但昂贵的医治费用让他们望而却步,不敢住院治疗,简单地配了一些保养药就回去了。后来,公公的病越来越严重,一天到晚气喘吁吁,唠咳不止,尽管找土方请医生熬中药吃西药,甚至求神拜佛名堂搞尽,都没有效果,就像下雨天背稻草——越背越重,病没治好,反而欠了一屁股的债。原想靠丈夫出外打工赚钱还债治病,谁知飞来横祸,弄得个家破人亡、人财两空。有人给她做介绍,劝她再找一个婆家,她不愿辜负丈夫的恩爱,几次都泪流不止,摇头回绝。她也曾几次生出念头,想结束自己的苦命一生,追随丈夫而去,但一看到年幼无知的儿子和年迈重病的公公,她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她说,她如果就这样走了,谁来照顾他们呢?真的于心不忍啊!
听到这里,我像被电触一般,全身为之一震,多么伟大的女性啊!在这物欲横流花天酒地的当今社会,又有多少人能了解和关注像她这样的弱势群体在人间底层所遭受的苦难和痛苦呢?又有多少人能像她那样心地善良、心灵圣洁和心境高尚呢?
我从身上掏出仅有的500元,递了过去。我知道这是杯水车薪,远远解决不了她什么问题,但我还是想以此求得一种自我安慰。她却双手直摆,脑袋摇得像货郎鼓一样,死活不肯接受。
从那时起,我有意无意地加大了清洁脚下那双皮鞋的频率,有空没空,三天两天,总要跑到她那里擦一次鞋,而且是不见她不擦。有时出差外地一个多星期,哪怕皮鞋灰尘再多,自己都看不过意,也坚持不擦,一到家中,行李一放,就找她擦皮鞋去了。在去擦鞋的同时,也免不了带一些糖果食品玩具之类的东西给那孩子。
一天下班的时候,天上突然间乌云密布,雷鸣电闪,下起了瓢泼大雨。我正行走在人行道上,突如其来的大雨使我措手不及,赶紧脱下罩衣顶在头上,一阵小跑来到了横穿芙蓉路的人行地道。这时,她牵着儿子,也飞跑着躲进了人行地道。见了那孩子,我随手将刚刚从店子里买的准备第二天做早餐的面包递给了他。我知道,他这时肯定饿了。
她拦住了孩子的手,“先谢谢伯伯!”要他先叫了我以后再接。
“谢谢伯伯!”孩子早已耐不住了,一边叫谢,一边早已把面包接到手中,狼吞虎咽起来。
“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我的心酸楚楚的。
见雨一时半刻停不下来,我向她招呼:“来!给我擦一擦!”随手拉过小竹椅,靠着地道墙壁,坐下来,把脚一伸,让她把鞋子擦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鞋子已擦得油光闪亮,雨还在下,但小了许多,我便匆匆忙忙付了钱,一阵风似地跑回了家。工作忙乎了一天,累得很,加上淋湿一身,回家后,赶紧换衣、洗澡、吃饭,早早就睡了……
第二天,我突然发现,身上的钱包没了。钱包里2000多块钱是小事,但里面的证件和票据却非常重要。我焦急万分,到处寻找。
丢哪儿了呢?难道不翼而飞了吗?我暗地里叫苦,哑巴吃黄连,不敢与夫人诉说,怕她又说我毛手毛脚,不长记性。我有一个总改不好毛病,每次出差回家,总要丢失点什么,比如说,牙膏、肥皂、毛巾,甚至短裤、背心什么的,总被夫人拿作笑柄,免不了被讥讽几句。男子汉嘛,自尊心还是有的,谁又愿意在家人面前丧失脸面,无言以对呢?
我左思右想,回忆起昨天的情景:下班时,下雨了,我将衣服顶在头上,跑入人行地道,后来又顶着衣服跑回了家。进人行地道时,钱包肯定是在的,因为我掏出过钱包,付了擦鞋的钱,唯一可能的是,付钱后,没有把钱包装进口袋,或者是在顶着衣服跑回家的途中钱包甩了出去。
哦!我终于想起来了。我在擦完皮鞋付了钱把钱包装入口袋并将衣服顶到头上的一瞬间,脚后跟似乎“啪”地一声响了一下。对了!那一定是钱包掉地下的声音。只是因为当时外面的雨声、汽车声嘈杂,加上我急急忙忙地要跑回家去,也就没有引起注意。唉!看我这木呆子脑壳,太粗枝大叶了,钱包掉了一点都没有察觉。
这时,我想到了她。她在现场,一定看到我的钱包掉了。我把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我也感到担忧,她会不会把捡到的钱包还给我呢?我想,她会还给我的,只要还给我,我就把包里的钱都给她,我只需要回那些对于我来说十分重要的证件和票据就行。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找到她经常擦鞋的地方,出乎意料,她竟不在那儿。抬头望去,人行道上人头攒动,南来北往,不远处有另外几个擦鞋的大嫂正忙乎着,独独不见她的身影。也许她今天换了一个地方,沿着人行道我从北至南,然后又折转身从南至北,认真搜索个遍,但始终不见她的踪影。我不甘心,跑到马路对面,从南到北又找了一遍,还是没有她。这时,我真有点着急了,难道她真起了邪念,躲起来了?一种猜想从我脑子里一闪而过。不!她应该不会那样!
这一天,我心如乱麻,连续几次又去了那段人行道,该找的地方都找了,该问的人也都问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扫兴而归。我沮丧极了,只能自认倒霉,哪个要你如此毛手毛脚粗心大意呢!我怀疑,我的眼光和判断力出了错。
过了几天,我上班再一次经过那段人行道,忽然间,听得身后有人在喊:“喂!老总。”是个女人的声音。我不是“老总”,便也没在意,继续向前走去。
这几天丢了那些东西,特别是丢失了那些证件和票据,心上心下的,烦躁得很,吃饭不香,觉也睡不好,早晨起来得晚,一阵洗涮、梳理,草草吃点东西后,上班时间就快到了。我从参加工作起就从未迟到过,今天单位有一个重要会议,我是唱主角的,可更不能迟到呀。想着想着,脚下的步子便不由得迈得更快。
“喂!老总!请等等!”还是那女人的声音,有点耳熟,正纳闷时,感觉有人在身后小跑着追来。
回头一看,我又惊又喜,竟然是她,几天来寻丝觅缝苦心寻找的那个擦皮鞋的女人。我停下步伐,满怀狐疑地看着她。只见她额头上冒着汗珠,上气不接下气,“老总,你是不是丢了什么?”
“是呀!”她这一问,我早已明白了一大半。
“那天,在地道内,你走后,我就发现了这个。”她气喘吁吁,扬了扬手中的那件东西。定神一看,这不正是我朝思暮想急切盼望着要找回来的钱包吗?不由得心中大喜。
“当时我打开一看,见钱包里有你照片的证件,就赶紧追了上来,那知道你走路起飞,一下子就不见了人影。”她一边喘气,一边把钱包递给我说,“我想你丢了钱包,肯定会来找的,就在那里等着。那知道等呀,等呀,不知等了多久,都不见你回转过来。”
“本想第二天再到那儿等你,哪知……”说到这儿,她的声音低沉下来。
“哪知什么?”我急切地问道。
“那天,因为淋了雨,受了寒,我儿子发起了高烧,一晚上尽讲胡话,我急得要死,守了他一通宵。要是他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可怎么活呀!”她眼睛里噙着泪花,话语里饱含着一种天性的母爱。
“后来呢?”我既同情又关切,很想知道她儿子的病情结果。
“后来在老乡们的帮助下,把他送进了医院,吃了药,打了针,现在好多了。”她嘘了一口气,面带歉意对我说,“实在对不起,这几天照看他去了,没把东西及时还给你,让你着急了。”
“快别这么说了。他好了就好!”我想起了一件事,迅即打开钱包,从里面抽出那叠钞票来……
她似乎知道我要做什么,话没说一句,转过身,头也没回一下,一溜烟跑了。
我站在原地,许久许久一动没动,是感动,还是惭愧,自己也无法说清……
作者简介:
刘克邦,文创一级,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省散文学会名誉会长,中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硕士生导师,湖南女子学院、怀化学院客座教授,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第四届毛泽东文学奖、中国作家杂志社征文一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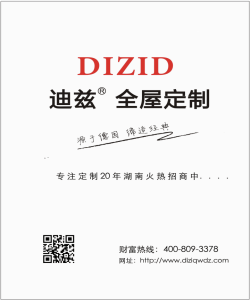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