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邦散文赏析 ▎疤痕
疤 痕
母亲,出生于湘西黔阳(今洪江市)的一个偏远山村,家境并不富裕,但勤奋读书,学业有成,在芷江师范毕业后,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僻静的故土,当了一名令人称羡的小学教师。
解放初期,贫穷落后的湘西,师资匮乏,学校简陋,教师稀缺,一个老师往往要承担多个班级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母亲无怨无悔,在艰难困苦的环境扎下根来,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废寝忘食,夜以继日,把满腔的热情和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山村的孩子。
由于长时期超负荷工作劳累和心力透支,加上父亲无故被打成“右派”服刑后遣送原籍农村的牵连,她遭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折磨,积忧成疾,身体虚弱,一天课下来,经常头昏眼花,站立不稳,倒在床上动弹不得。
那时,我年纪虽小,但已经懂事,深知母亲的辛酸与不易,每天放学以后,提起柴刀和扦担(一种木棒做的长长的圆圆的中间粗两头尖挑柴用的工具),就到学校后面大山中砍柴,将那些丛生在坡顶上、山腰中、陡坎下、丛林里的野树杂枝一根根割断砍倒,一束束对齐刀口处,堆集在一起,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分成两堆,寻找一根柔软的藤条或者是既长又直且带韧性的纤细树枝,将枝尖一头拧成一个麻花状的扣眼后,插入一堆柴火下,拦腰一扣,一锁,一拧,反插过去,捆成一捆。如此反复,再捆一捆。然后将扦担一头插入一捆中,腿一蹲,肩一挺,挑回家来。如此一天一挑子,一挑接一挑,天天不断,保证了家里一日两餐生火烧柴不缺,也省去了一笔不小的费用开支。
一天,在离家三里地之外读完书的我,像往常一样,下午放学回到家中,书包一扔,拿起柴刀和扦担就往外走。母亲病倒在床已有好一些日子了,见我又要上山,支撑着上半个身子,对着我:“孩子!今天就算了,在家做作业,别去砍柴了。”声音微弱,话语简单,但蕴藏其中的爱,亲切、深厚、博大,暖流了全身。我止住步子,迟疑了一下:“柴堆里的柴不多了,今天还早,我还是去吧!”说完头也没回地走了。“那你早点回呀!”母亲拼着力气在身后叮嘱道。“知道!”话刚答完,我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两眼模糊不清了。
一路快步,我爬上后山,翻过几道梁,攀扯着杂草树枝,左寻右找,来到一处平常少有人到的背弯山洼里,袖子一捋,往手心中吐一把口水,弯腰埋头,挥舞起柴刀来。
今天算是找中了地方,这里野树连片,灌木丛生,茎条粗壮,枝叶茂密,是最理想的砍柴之处,我欣喜若狂,越干越欢。一会儿功夫,羊筋、桎木、苦楝、金刚、腊树,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杂木枝条,被我从荆棘中拨开,从茅草中分出,齐根部砍断,去掉繁枝茂叶,一根根、一把把,躺在我的脚下,整齐地排成长队,仿佛等待着我的检阅。
太阳就要落山了,柴也砍了不少,我正要将柴收拢起来进行捆扎,忽然听见头顶上半山坡有人在大吵大闹。抬头一看,是塘冲湾里的两个同龄伙伴,一个叫爱河,一个叫多吉,也是上山来砍柴的,不知咋地为了一点小事发生口角,你一句来,我一句去,互相骂起娘来,且越骂越凶,越骂越难听,骂着骂着,两人竟打起来了。
见此情景,我停下手中的活计,双手合在嘴边作喇叭状,向上面高声劝阻他们,“别打了!有什么事情说得清嘛!”不知道是听到了还是没听到,两人还是互不相让,纠缠在一起厮打,丝毫不肯放手。我正要爬上坡去拉开他们,可能是爱河处于下风,吃了亏,竟像一头发怒的狮子,松开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照着多吉身上砸。多吉一躲,没砸着。爱河捡起一块石头又砸,又一躲,还是没砸着。爱河恼羞成怒,四下寻找石头准备再砸。许是多吉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凶狠吓住了,不想矛盾进一步激化,便放了让:“我怕了你,我们讲和好不好?”但爱河不依不饶,继续寻找石头,以图报复。惹不起躲得起,多吉撒腿就往山下跑。竟然直接就跑到了我的跟前。他一把抓住我的衣服,躲在我的身后,感到有了安全感以后,又向上面挑衅起来:“狗娘养的!有种的就砸呀!”。我连连向上面摆手,放声向爱河喊道:“别砸了!别砸了!这样会伤人的!”哪知道,话音刚落,只听得“嘭”的一声,一块石头不偏不倚,落到我头顶正中。顿时,我眼前一黑,金星直冒,一股凉飕飕的液体顺着太阳穴两边直往下流。一抹,是鲜红鲜红的鲜血,头一晕,扑倒在地,什么也不知道了。
见我倒在地上,血流如注,两个惹事的伙伴吓得脸都白了,骂也不骂了,架也不打了,凑拢来,跪伏在我的身边,喊我,拍我,摇我,掐我……一阵手忙脚乱,仍然无济于事。还是多吉聪明,想起大人们平常止血的办法,转身寻来一把不知名称的野生植物,放在口中嚼细嚼烂后,托扶着我,拨开我的头发,敷在我的伤口上。这一招还真灵,草药上去,血马上被止住了。
不知过了好久好久,我慢慢地苏醒过来。看着我浑身鲜血,气力虚弱,他们俩害怕起来。特别是爱河,知道自己今天闯下了弥天大祸,像一只惊弓之鸟,惶恐不安,不知所措,反复地呼唤着我,并哀求我原谅他的过错,不要将此事告诉大人。我半睁开眼,看着他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又在尽心尽意地照顾着我,微微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夜幕降临,他们两人,一左一右搀扶着我,上山,过岭,下坡,一步一步挪动着,慢慢地回到了村子。
回到家里,已经是掌灯时分,我生怕母亲知道了伤心,悄悄地溜进屋,躲到房子一角。母亲躺在床上,见我这么晚才回,且一声不吭,感到十分奇怪,硬撑着身子爬起来,点亮煤油灯,走到我的跟前一照,只见我蓬头垢面,浑身是血,眼睛低垂,脸色苍白,瘫倒在地上,被吓了一大跳。在她的反复责问下,我有气无力地将事情的前后经过告诉了她。母亲把我拉到桌子边坐下,揭开我头上的草药一看,只见我脑门顶上,血肉模糊,头骨塌陷,黑糊糊地张开一个大口子,心痛得泪水泉涌般地直往下流。
那天晚上,母亲拖着重病的身体,背着昏迷不醒的我,就着手电筒的微光,踉踉跄跄地在崎岖山路上奔忙了一夜。她四处求同事,找亲友,终于借来了钱,请来了远近闻名的郎中,买来了最好的创伤药,硬是把我从残废的边缘,不,准确一点说,应该是死亡的边缘生生给拽了回来。
我的舅舅、姨父和表哥们知道情况后,急急赶来我家看我,对我挨砸一事情绪激动,愤愤不平,找到爱河家一定要给个说法,提出必须负担全部医疗费和营养补助费的要求,如不兑现就搬床铺抬柜子捉鸡鸭撮谷。母亲的同事和邻居们也纷纷为此打抱不平,一致认为爱河家赔偿经济损失不可推卸。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也表示要为母亲做主,责成爱河家承担全部责任。
在众口一词的讨伐声中,母亲却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意想不到的决断,她不许亲属们采取过激措施,也感谢同事、邻居和干部们的关心,对着低头不语无所适从的爱河父母说:“我家孩子被你家孩子打破了头,赔偿医疗费和营养补助费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我知道,你们家里也很穷,要赔偿几百块钱,一是现在拿不出,二是向亲戚朋友借得到,那也很难还得清,肯定会好多年都翻不了身的,我不忍心你家为此倾家荡产,无法生活,只能自认倒霉,治伤欠的帐自己慢慢来还。还好,老天开恩,我儿子命大,没有发生更悲惨的后果,只希望爱河记住教训,以后再莫惹祸就行了。”话刚说完,爱河父母“扑通”一下跪在母亲的面前:“谢谢邱老师的宽宏大量!我们全家人万分感谢你!”边说边连磕了几个响头。“快起来,别这样!”母亲含着眼泪把他们扶了起来……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母亲早已不在人世。有句话,叫做“好了伤疤莫忘记痛”,每每触摸到头顶上那块凹下去的疤痕,我记得的不是自己当年被击打的痛,而是母亲对儿子那份痴迷的爱,对他人那份如大海般的宽容和大度。

幸福一家子。2013年8月5日,作者与夫人、儿子参观韶山后,在韶山火车站广场留影。
作者简介
刘克邦,文创一级,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湖南省散文学会名誉会长;中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科技大学硕士生导师,湖南女子学院、怀化学院客座教授。出版散文集《金秋的礼物》《清晨的感动》《自然抵达》《心有彼岸》;在《中国作家》《散文选刊》《散文百家》《芙蓉》《湖南文学》《创作与评论》和《文艺报》《中国文化报》《中国财经报》《湖南日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200多篇。获全国第六届“冰心散文奖”、湖南省第四届“毛泽东文学奖”、财政部全国征文一等奖、《中国作家》杂志社征文一等奖、长沙市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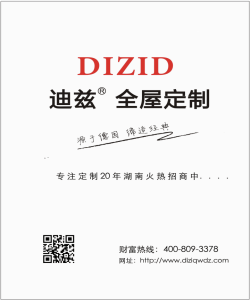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