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精选 ▎春 叔 (文/戴志刚)
春叔
文/戴志刚
若非前两天和春叔的二丫头在街头的一次偶遇,春叔——这个已经离开人间30多年的男人,极有可能不会被我主动地再记起来。时间更多的时候是扮演一个黑洞的角色,会吞噬很多人生的过往,让记忆稀释,让情感淡漠。哪怕被淹没的某些部分,曾经是那么的美好。
春叔去世那年,虚岁36岁,听说是肝癌。在湘西北农村,传说男人虚岁36岁是人生一道坎,民间讲究较多,特别是得摆酒宴客,以示冲灾治妄。春叔原本也是定在下半年某个日子摆酒的,但他没有等到那天,似乎更加证实了“36岁一道坎”的民间说法。我之所以记得春叔走的那年36岁,也大致是他去世后,大人们在一起总把这个36当作洪水猛兽般地议论。
春叔在当时贫瘠的麻雀湾,是个颇为特别的存在。特别在于两个字,高和帅。他当年是湾里个头最高的人,这毋庸置疑,平时乡邻们一起出工做事,他身姿挺拔的样子,用“鹤立鸡群”这个成语形容一点都不亏。至于“帅”,那个年代好像还没有赋予这个汉字形容一个人气质的概念,我今天把这个字送给他,是源于我的印象里,他周正的面相、优雅的笑容以及总是干净的穿着,与周遭乡亲们泾渭分明。他的二丫头在前两天和我的谈论中,也用“好帅”一词表述了她父亲在她记忆里的模糊印象。她说她已记不清她父亲一些具体的事情,但她说父亲“好帅”时明显骄傲的神色,与我记忆里对她父亲的印象是完全吻合的。
按理说,我对春叔的印象应该也是模糊的。他去世那年,我和他二丫头都只有7岁。但在谈论中,我发现我比二丫头记住她父亲的事情还要多——好些事情,她基本没了印象,我还记得大致的轮廓。这就有点奇怪了。晚上,我躺在床上认真地想,临天亮时终于想明白,原来我一直记着的,是春叔的好。
春叔不只是人长得好,性格也很好,说话又不像麻雀湾里其他汉子出口那么粗鄙。对我们这些孩子,总是满面春风,欢喜得紧。春叔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家境在当时的麻雀湾并不算好。那个年代,农村还在搞大集体,他家吃饭人多,做事的人少,挣工分当然也少,连吃饱饭都比较困难。这并不妨碍每次我们去他家玩,还总能吃上一碗鲊辣椒面糊拌饭,或者一顿水煮红苕之类。
年少不知事,只知道谁家大人好,就乐意到谁家玩,到了饭点也不回家。在麻雀湾,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很多,每次去春叔家玩耍,总有四五个甚至更多。春叔家有一只煮饭沥米汤的大黄钵,每次到了饭点,我们还没回去的话,他就要凤婶和上一满钵鲊辣椒面糊。开饭时,连他家三个女儿总共七八个孩子,一个个吵着闹着,往碗里舀上几勺鲊辣椒面糊拌饭吃。等孩子们吃完,他和凤婶上桌时,黄钵早已底朝天,像被狗舔似的干净了,他们只能吃光饭。这样的次数不在少数,春叔从来没有表现过不快,或者驱赶我们,我们在桌上吵吵闹闹争饭抢菜时,他还呵呵地笑,好像在看一场什么有趣的节目。
麻雀湾20多户人家,家家都有孩子,我们并不是在每一家都能像在春叔家吃上饭。有些人家,到了饭点,就会或暗示或明示要我们回家去。当然,厉声驱逐我们的人家也会有。现在想来,日子都过得紧紧巴巴的年代,湾里每家每户其实都没有太多的余粮,乡邻当时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只是我们这些顽劣的孩子,当年那些不懂事的行径,不知给人家造成了多大的窘迫。
和春叔二丫头聊起这些事,她笑说,她父亲对我们这些孩子的喜欢,是源于重男轻女思想,他对她们三姐妹的管教还是比较严格的。或许春叔确实有这种思想,一连生三个丫头,在当时的农村,脸上总有挂不住的时候。有一次,春叔在我家串门聊天,半开玩笑说要将他三丫头和我弟弟调换,我母亲居然还当了一回事似的,与他探讨了这个问题。但要用这个观点来看春叔纵容我们常在他家胡吃海喝的行径,是站不住脚的。那个年代吃饱肚子是头等大事,我们在他家胡闹一顿,他家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接下来定然会困顿很多。如若春叔没有对孩子真正的欢喜,断然不会对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纵容。况且,他也一直允许几个女儿和我们一起玩闹,从不见呵斥过她们。甚至连他家的猫和狗,也少见他呵斥。在农村,指狗骂猫的事情常有。而他家的猫碗和狗钵,畜生吃过之后,都被春叔洗得干干净净归置在灶头,绝不会被随脚一踢,打入犄角旮旯。
春叔算是个手艺人,他是木匠,能做得一些小家小件,大活可能差点。他的手艺没有拜过师,完全是看别人做活时的瞟学。凭着聪明,他做出来的桌椅柜台也还精致,有模有样。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割资产主义尾巴的聒噪声终是歇了些,农村思想和余钱才活泛起来的人家,都想着怎么添置一些实用的物品,来改善家居条件,一些手艺人也总算能凭一技之长赚些家庭补贴。春叔瞟学的木工手艺终于有了用武之地,隔段时间就有周边乡邻请他去,帮着打些实用的家私物什。春叔也从不虚言妄为,自认能拿得下的活就接,拿不下来的就拱手致歉。那时的农村,谁家没有儿子大抵会被人欺负。春叔家虽是湾里仅存的独姓户,家里又没有儿子,但凭着他得体的谈吐,谦逊的处事,倒也赢得不少口碑和尊重,没见谁家明里暗里对他家使过绊子。
那年,母亲想要打一个多层的水缸架,除保护那只硕大的水缸外,还能搁置厨房杂七杂八的物品。于是把春叔请到家里。春叔扛着装着斧子、锯子、凿子的工具箱,带着那条小黄狗来我家时,依然穿着一身干净的白衬衫,不像是来干活,倒像是来走亲戚。在我的印象里,春叔四季的衣服似乎都是浅色,稍热起来,基本上就一袭白衬衫了,哪怕到了七八月最为炎热的“双抢”季,下田干活,他也总穿着一件背心,绝不会如其他农村汉子一样光背亮膀,这在当年的麻雀湾也是独一份的存在。
春叔在我家做活的那两天,总有我们几个小伙伴围着他转,看他把一截截原始状的树筒子,以劈刨锯凿等各种动作,慢慢变成有棱有角的可用之材。他对孩子似乎有天然的吸引力,他在干活的时候会和我们说一些打趣的话,也不介意我们动他的斧子,摸他的锯子,甚至还会叫我们给他递工具,这是我们乐此不疲的原因。更让我们觉得好玩的是,他弹墨线时,会让围观的孩子轮流参与。我的两个手指头捏着细细墨线,轻轻拉起,再突然放手,“嚓”的一声轻响,细线在平整白净的木头上弹现出一条笔直的黑线。在春叔带着几个孩子做手工的欢乐氛围中,材料终于凑成了成品。可当春叔要把架子套上我家那个大水缸时,可能是他在和我们的互动中,疏忽了某个卯榫的角度,发现围水缸的框架做小了,根本套不进水缸。他讪讪地笑了几声,只得拆了框架部分进行返工。活干完了,母亲付春叔酬资,他死活坚辞不收,只歉声说东西没做好,浪费了东家的材料云云。春叔去世多年后,我家重新修房子,处置那个水缸架时,母亲重提此事,爷爷在一旁还突然说了一声:“好人呐!”。
没过多久,我和春叔几个丫头一起上学时,就隐约听说春叔得了病。人吃五谷生百病是件很正常的事,我们年少无脑,没当回事听。又没过多久,有一天,春叔家几个丫头都没上学。我晚上散学回到家里,听到了春叔去世的消息。
春叔没有葬在麻雀湾,说是葬回他的姓氏祖地。出殡那天正是周末,麻雀湾的人都加入了送葬队伍,包括我们这些受过春叔恩惠的孩子,一直走了很远很远。春叔养的那只小黄狗,也一直跟着出殡队伍,在春叔的棺前棺后钻来跑去。春叔下葬后,那只狗再不肯跟着同去的人同回,趴在坟前总不起身。后来,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那只狗。
春叔去世一两年后,凤婶带着三个丫头改了嫁,由此搬出麻雀湾,大家慢慢疏联络。10多年前,我在县城遇一高挑美女,似在哪见过,好面熟。待她叫了我,报出名号,我才知是春叔的三丫头。春叔走的那年,她不过三四岁。她的个头,周正的五官,眉宇之间的神韵,像极了当年的春叔。

作者简介
戴志刚,网名刚子哥哥,常德临澧人,湖南省作协会员,湖南散文学会会员,临澧作协副主席,毛泽东文学院中青作家班第十八期学员,供职于临澧县太浮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在《解放军文艺》《湖南文学》《散文百家》《湖南日报》《湖南散文》《中华文学》《战士报》等报刊发表作品逾百篇,著有散文集《风雨起心澜》《踏歌而行》《凉月微弄》三部,曾获丁玲文学奖和常德市原创文艺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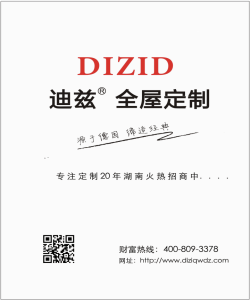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