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明月长作伴
老家居泸溪山巅之上,因取名“峦”。青年人喜欢这种解释,说直截了当。杜甫《望岳》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志向远大,卓尔不群。然而,老辈人却说因见“鸾”而得名。鸾是古代中国神话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说文》:“鸾,神灵之精也赤色五彩,鸡形,鸣中五音。”汉、晋把鸾鸟视为春神之使者,以及东王公与西王母的象征。《山海经》:“女床之山,有鸟,其状如翟,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不管是“峦”还是“鸾”,在这里都是吉祥物和精神的化身,都有着深刻的寓意。山巅贵中贵是水,恰好山巅弯里水源充沛,故“弯”成这个“湾”。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一个寨子的团结尤为重要,这大概就是家乡取名“鸾团湾”的缘由吧。

作家符云亮接受央视记者采访。
造成寨子第一次大搬迁是因水的缘由。明末清初,地主一对双胞胎女不幸落入水井淹死了。地主气得向水井里倒了1吨草木灰和3吨鸡粪,结果水渗入山下河边了。没有水了,寨子里的人不得不向永顺、龙山、张家界方向迁徙。不到两年里,2000户大寨子搬剩不到几十户人家。第二次大搬迁是因交通的缘故。随着改革开放,人民逐渐富起来,少部分人进城购房了,大部分人从山上搬至山下319国道两边居住,尤其是近几年政府出台折除闲置老房子复耕地的奖励政策,就这样,百来户老寨子拆剩不到20栋老房子了。
村长来电话说:“老房子放烂怪可惜的,还不如响应政策号召可得一笔补偿款。”我不加思索地说:“不拆!”我很生气地挂了电话。发小打来电话,说寨子里比我屋还新的都拆了,过了这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叫我三思莫和钱过不去。我说就算全寨只剩下我一家也不拆。叔伯爷儿们见我如此坚定也就不再劝我了,说我在城里发了财根本不在乎那几个补偿款。

符文蔚的速写画《老房子》。
看来这些年大家的确富裕了,个个都豪起来,连屋顶瓦都没下就直接用挖土机推。老房子伴随着一声声轰隆隆的响声,一幢接着一幢倒砸在地上,瓦碎得满地都是。夕阳西下,大家拿着补偿款欢天喜地地离去,而我却伫立在老房子面前久久不愿归去。此时此刻,我的五脏六腑、血液、呼吸似乎都凝固在老房子上,我犹如一尾刚问世的精子,正奋勇奔向老房子这温暖的子宫,似乎能清晰地感受老房子的脉动。
“天快黑了,儿子一个人在家里。”老婆催促我上车回城,而我却没憋住,一颗泪从眼角滚下来。我终于明白娘当年为何责斥老表拆老房子,为何每经过她娘家老房场都会情不自禁地落泪,这不仅是对先人的一种追思,还是对根的一种无限眷念。老房子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种潜在血脉深处的情结,一种精神上抹不去的胎记。老房子是儿时永远的童谣,人生弥足珍贵的记忆;老房子是青春的壮歌,承载着我的喜怒哀乐;老房子是心灵旅归的港湾,安抚着我的得失成败;老房子是人生最执著的守望,梦里最乐此不疲穿梭的地方。
一个清晨,老婆告诉我,她要把乡下老房子翻修一下,把屋前坪场加宽2米并保大堤坎,屋顶上的老瓦换上琉璃瓦,破旧的偏房改为砖木结构新房,还计划加修院围墙和院大门,这确实让我吃惊不已。老婆平常从不买时髦昂贵的衣服,连化妆品都很少买,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分用,可这次少说也得花上十来万元。虽然老婆向来勤俭持家,但她却肯为我下血本。这就是我从长沙娶回的老婆,一个愿从省城随我到吉首小山城扎根的女大学教师。老婆在大学是教体育舞蹈的,干事总是雷厉风行,豪气里裹着胆识,磅礴中富有精神。两个姐姐闻悉跑来阻劝,说父母都不在了,没有必要花这么一大笔钱。老婆轻言细语地说:“只要咱阿亮(我的乳名)高兴,花再多钱我都乐意。再说娘在世待我如亲闺女,我不能因娘不在了就让她魂栖破烂屋。”说得我两个姐姐噼里啪啦直掉眼泪。
虽然结婚十多年,但我却很少跟老婆讲起我在乡村的故事。那时候不像现在的小孩有玩具和手机玩,但我们的童趣一点不比现在孩子少。滚铁环、玩陀螺、打纸片、拼大刀、射箭等等完全自制,乐趣也是完全自寻。我最喜欢在家门口石板路的石板上画画,好多人夸我画得不错。过去这条石板路很热闹,尤其是到热天,乘凉拉家常的、下打散棋的、唱辰河高腔的、纳鞋底绣花的,不过我还是喜欢听瞎奶奶讲故事。她可是寨上神人,似乎方圆十里八寨没有她不知道的事。后来我能写点东西,她算得上是我写作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她常说我家风水好,只可惜屋前下方有一排牛栏,因此,难得富裕。她还说,一旦人强过牛就会发生牛死栏倒。其实不是寨上人有意针对我家,而是我家起屋在后头。伯母托一个老司(巫师)开光一把杀牛尖刀,叫我娘悄悄埋在堂屋门前土中。说来也怪,堂屋门前那两栏牛总是瘦骨嶙峋病歪歪的。后来,虽然不全如瞎奶奶所说,但我大学毕业第二年全寨都换上“铁牛”耕田地了。
小学五年级,我就去小镇念书,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每次我会站在家门口喊娘,娘应声回来开门给我做好吃的。如果三声后没听到我娘应声,伯母就会应声叫我进她家,一样会给我做好吃的。总之,那时回家是我最甜最开心最幸福的日子。不过我念完高中后就越来越怕回家了,好想逃得远远的。高中时,校大门口喜报墙几乎成了我的专属,可因为贫穷我被迫离开眷念的校园,但是我没有放弃梦想,依然笔耕不辍。或许,是现实与理想太不对称,我成了大家冷嘲热讽的对象,尤其是乡亲。他们不仅对我百般挖苦诋毁,还不准他们的孩子与我往来,一时我成了寨上十恶不赦的人。好多年后,我明白这是乡亲对我爱的一种表达方式,如同一个诗人所言,“是鸟就不要迷恋大海,是鱼就不要迷恋天空”,他们希望我迷途知返,抛去幻想回归现实中来。虽然娘不理会他们,但我的伯母就不是缄默相对,而是毫不客气地怒斥他们“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还说我是她接生孩子中时辰最好的,将来准有大出息。
知儿莫若母。娘知道我不会跟寨子里的人一起出去,一定会独自出去打工。穷家福路,娘把冬天用来买碳攒的1500元全塞给我。临走那天,娘不说话,只是眼角默默闪着泪花。上世纪90年代,深圳不比现在好找工作,我露宿街头睡山坡坟地3个月才找到一份备料的工作,说白点就是在一家加工珠宝盒搬木头。不管怎样算是在深圳有歇脚的地方,也是不幸中的万幸。经过半年打拼,加之我有写作特长,我从搬运工被提拔为行政助理,经7个月后我升到副总经理。无论怎么变,每次发工资我只留100元,其余都寄给娘,唯有这样我心才有所安。我在副总经理位子上干了不到4个月就去广州日报社做事,总算找到了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当记者。我写信告诉娘,娘很开心,不过伯母不知记者是干啥的。在这之前,不光是寨上,就是小镇也没出过记者,可娘知道,娘的堂二哥就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记者,也就是沈从文在他的《泸溪·浦市·箱子岩》文中提到的那位了不起的写了《日本不足惧》的龚德柏先生。伯母听了特高兴,逢人就讲我在广州混出头了,当上了记者。一时村里人和我昔日的同学纷纷向我涌来,托我帮忙谋事做。可遗憾的是,伯母没等到我春节回家就仙逝了,从此我只能面对一堆黄土与伯母倾诉心声了。
2000年8月,我接到吉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突然回家,娘大吃一惊,以为我在外犯了事被别人辞退了。当娘听说我要上大学了,一把拖着我直往葬我的爹的山头去。娘叫我给爹磕头,说一定是爹在天上护佑我。当夜,娘撬开我家房地板把存放的钱一股脑都取出来送我,我终知寄给娘的钱娘从不花,一分不少都为我攒下来了。
几年后,我在城里娶妻生子,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记得我买下第一套房子,原想像别人请酒设宴庆贺一番,可娘极力反对,说我城里的房子柱都没沾地,充其量就算寄寓而已。虽然城里的那套房子的造价远远高于乡下一栋房子,但娘的话自有娘的道理。是的,城里能容下我们的肉身,却留不住我们的灵魂。这也是我以后买房不请酒的缘由。每次要接娘来城里享福,可娘都以不习惯城里生活婉拒。娘情愿一人住在老家守着老房子,为爹娘、为自己、也为我们守住老房子。
儿子符文蔚问老房子翻修好是否换一把新锁,我和老婆异口同声地说还用老锁。老锁是娘留下来的,一把独钥匙。自娘去世后,一直交给二哥家保管,而我们每次回去都是提前给二哥打电话。“那多不方便。”儿子说。老婆说:“便于你二伯家放东西,也便于你2个姑姑走亲戚可进家休息。”儿子毕竟才11岁,自然不懂更深层的意思,天真地睁大眼睛说:“新锁都有4把钥匙,每家一把不是更方便吗?”我意味深长地说:“老锁更有回家的味道。”儿子似懂非懂点点头又马上摇头,我想他长大后自然就明白其中的道理。
老房子翻修好了,古老中又添了几分鲜亮与壮观。有人说好,也有人戏谑“有钱就任性”,大家七嘴八舌讲个不停。我知道没有儿子居住的老房子,最多不过四代,终会淹没在时光中。老婆特意挖来2株娘喜欢的桂花树栽在房前,我知道老婆种下的不是树,而是对娘的怀念。儿子情不自禁地给老房子画了一幅速写,说带回城挂在家中以作留念。境由心生,清风明月长作伴,高山流水永相知。或许,老房子注定只能定格在我和我老婆的记忆里及我儿子的画中,用一生去回忆,一生去想念……(文/符云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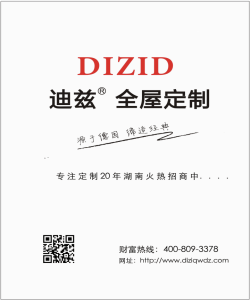
 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
湘公网安备 43010202001363号